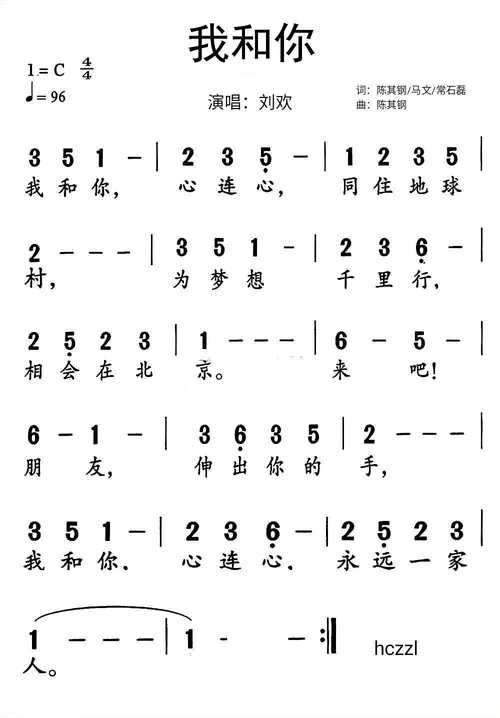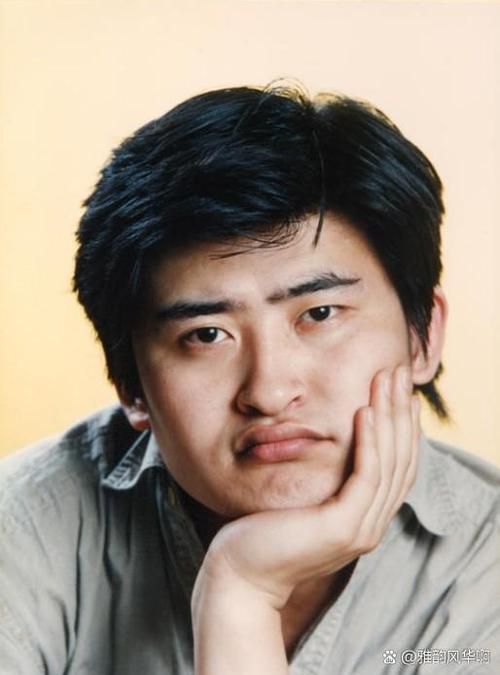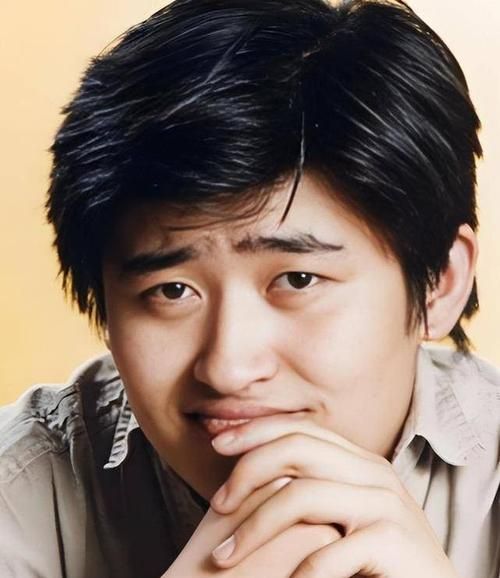清晨七点半的市文化中心办公楼,三楼东侧的办公室已经亮起灯。刘欢欢坐在工位上,指尖划过文件,眉尖微蹙——这是她刚接手的非遗保护项目申报书,堆了整整三大摞。桌角的保温杯冒着热气,旁边却压着一张泛黄的纸,上面是大学时手写的我和我的祖国歌词,墨迹边缘还有没擦干净的泪痕。
没人能把“事业单位职员”和“业余歌手”这两个标签,像刘欢欢这样拧成一股劲儿。在单位,她是出了名的“刘干事”,每天都泡在资料室里,整理老照片、走访老艺人,为了给濒危的皮影戏申请非遗基金,她曾连续一周蹲在村里,跟着传艺人学唱腔,晒得黑了两个度;下了班,她换上演出服,成了酒吧、社区小剧场里的“欢欢老师”,弹着吉他唱民谣,嗓子清亮得能穿透喧闹。
“第一次知道她会唱歌,是我们单位年会。” 文化中心的老王师傅抽着旱烟,眯着眼睛回忆,“那时候年轻,推她上台,她脸憋得通红,就唱了首映山红,没伴奏,清唱。结果唱到一半,底下全哭了——你说怪不怪?人家是越唱越紧张,她倒好,越唱越有劲儿,唱完鞠躬时还绊了自己一脚,把大家伙儿逗得前仰后合。”

就是那次“意外走红”,让刘欢欢的“副业”慢慢有了起色。2019年,她抱着吉他去街边演出,被一个做独立音乐的朋友拍下来传到网上,视频里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唱的是自己写的老街坊,歌词里有“巷口卖糖的老爷爷,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偷拿你一颗糖吗” ,底下有人评论:“这声音,像小时候在奶奶家听的收音机。”
没想到,这条视频被市音乐家协会的人看到,问她愿不愿意参加“群文之星”选拔赛。刘欢欢当时正忙着给非遗项目做台账,扔下手里的笔就问:“参赛会影响工作吗?” 对方摆摆手:“你这样的人唱歌,才叫有根。” 最终,她拿了全市第三,上台领奖时,手里还攥着刚写好的皮影戏调研笔记。
有人问她:“你有这本事,干嘛不辞职当歌手?天天泡在单位里,多屈才?” 刘欢欢当时正对着镜子练孤勇者,听见这话,笑了:“你见过哪个歌手,唱着唱着就去查非遗档案的?我觉得有意思啊。” 她说,单位的工作让她看到“根”——那些快要被遗忘的老手艺、老歌谣,不是冰冷的文字,是活在人心里的事儿;而唱歌,是把这些事儿讲出去的方式。“有一次唱茉莉花,后台有个阿姨拉着我的手说‘姑娘,你唱的跟我小时候外婆唱的一个味儿’,你知道那时候什么感觉吗?就像…就像你种的花,突然有人告诉你‘它好香’,比拿奖还甜。”
当然,也有“翻车”的时候。去年冬天,她参加一个基层文化下乡活动,要去三个村子演出。早上七点出发,先是去山脚下的李村,雪下得大,山路打滑,她抱着音响在泥地里摔了一跤,演出服全是泥,她没顾上换,上台就唱好日子,村民拍着巴掌喊:“刘干事,你这一跤摔得,比电视上的还好看!” 中午在王村吃食堂,食堂阿姨给她盛了碗热汤,她端着汤碗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,边喝边听老婆婆唱山歌,下午又跑到张家,教孩子们唱少年中国说,孩子们跑调跑得厉害,她也没急,就一句一句带着他们唱,夕阳照在她脸上,汗顺着脖子流下来,她笑得跟孩子一样。
如今,刘欢欢的手机里存了两个相册,一个是“工作档案”,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会议记录、老艺人访谈录音;另一个是“舞台瞬间”,里面是她站在不同舞台上唱歌的照片——有简陋的社区活动室,有明亮的剧院,还有泥泞的乡间小路。前阵子,她刚写完一首新歌,叫办公室的窗,歌词里唱:“我坐在办公室的窗前/看阳光爬上文件堆/但我的耳朵里/总听见有人在喊‘再来一首’”。
有人问她:“刘欢欢,你累不累?” 她正在给非遗项目贴邮票,听见这话,抬头笑了笑,把邮票按在信封上,说:“不累。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干两件自己喜欢的事儿——一件是让老祖宗的东西活下来,一件是让我的歌飞出去。这两件事,都是在给日子添糖啊。”
或许,这就是最动人的地方——真正的热爱从不是“非此即彼”,而是把平凡的岗位变成舞台,把普通的日常过成诗。就像刘欢欢,她既是档案里那个一丝不苟的“刘干事”,也是舞台上那个光芒万丈的“欢欢老师”,而她最想做的,永远是自己——那个既能沉浸在一堆旧资料里,也能在一首歌里倾尽所有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