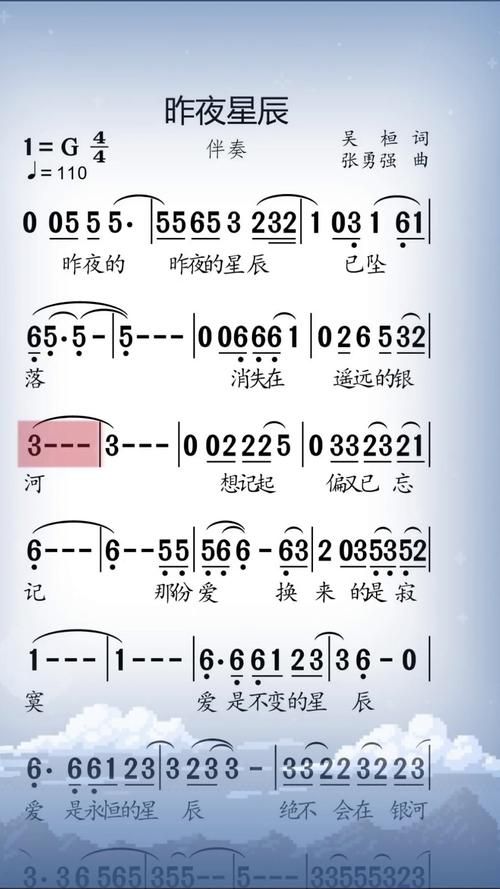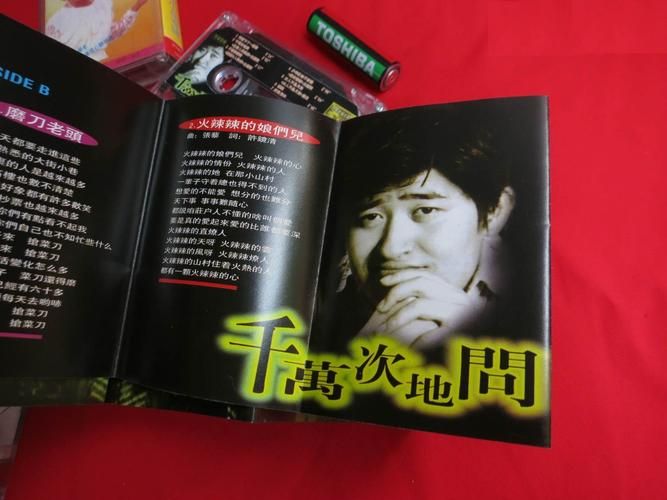1963年出生的刘欢,在大众印象里,永远是大唱好汉歌时穿着红衬衫、一头卷发的重量级歌手,或是中国好声音里戴着标志性黑框眼镜、幽默毒舌的导师。可若你把时间拨回1974年,北京第159中学的初三教室里,这个如今站在舞台中央的男人,不过是个戴着眼镜、有点腼腆的15岁少年——而他的“初三籍”,藏着一个关于饥饿、热爱与时代齿轮的青春故事。

1974年的冬天,铝饭盒里藏着半块窝头
刘欢的初三,是在“上山下乡”的浪潮尾巴度过的。彼时,城市中学生毕业后除了留城,很大一部分要去农村插队,刘欢也没能例外。“那时候每天最大的事,就是怎么对付饿。”多年后他在访谈里笑着回忆,“上课的肚子咕咕叫,比老师讲课的声音还大。”

他的同桌是个瘦小的女生,两人常分着带去的午饭——通常是母亲蒸的杂面窝头,酸得蹙眉,可咬一口就浑身发热。有时候课间操,他会偷偷溜到操场角落,从棉袄内兜里摸出颗水果糖——那是父亲用粮票换来的奖励,奖励他昨晚在家用二胡拉的赛马。
那时的北京,胡同里的收音机整天咿咿呀呀播着样板戏,可刘欢偏爱躲在学校音乐教室的门后,听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琴房的旧钢琴少了个琴键,他就用手指按住旁边的键,硬是把旋律凑了出来。“那时候谁要会弹个生日快乐,就能在年级里横着走。”他调侃道,眼里却闪着光。
“初三籍”的“特殊凭证”:一张文艺汇演入场券
真正让刘欢的“初三籍”与众不同的,是那张泛黄的“北京市中学生文艺汇演入场券”。1975年春天,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,指着窗外的杨树说:“刘欢,学校要搞汇演,你们合唱队缺个领唱,你去试试。”
他紧张得手心冒汗——要知道,他之前最多在班会课上唱过学习雷锋好榜样,连正儿八经的舞台都没上过。“当时我穿着打了补丁的蓝布校服,站上台时腿都在抖。”可当他开口唱红星照我去战斗,底下几百个同学突然安静了,连教导主任都忘了记笔记。
他们班拿了二等奖,奖品是每人一本毛主席诗词选集和一支英雄牌钢笔。刘欢把那张红色入场券小心翼翼夹进了书里,旁边用钢笔写着:“1975年,我的声音第一次有了回声。”
从初三教室到世界舞台:那颗种子早发了芽
初三毕业,刘欢没有立刻下乡,而是留校当了代课音乐老师。他常给学生们弹牧神午后,说:“音乐不只是唱歌,是让心里的话飞出来。”1981年,他考入国际关系学院,主修法语,可晚上抱着吉他跑遍酒吧驻唱的日子,早就从初三那年藏身琴房时开始了。
如今回头看,刘欢的“初三籍”哪里只是个时间节点?那是饥饿中长出的热爱,是破旧教室里飞出的梦想,是那个特殊年代里,一个少年用歌声对抗困境的倔强。就像他在弯弯的月亮里唱的:“遥远的夜空,有一个弯弯的月亮。”而1974年的初三夜空里,那颗叫“音乐”的月亮,早就挂在了他心上。
所以下次再听刘欢唱歌,不妨想想:那个在初三教室里分窝头的少年,是怎样把半生的风霜揉进旋律,唱成了我们这代人记忆里的背景音?毕竟,最好的故事,从来都是从“曾经”开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