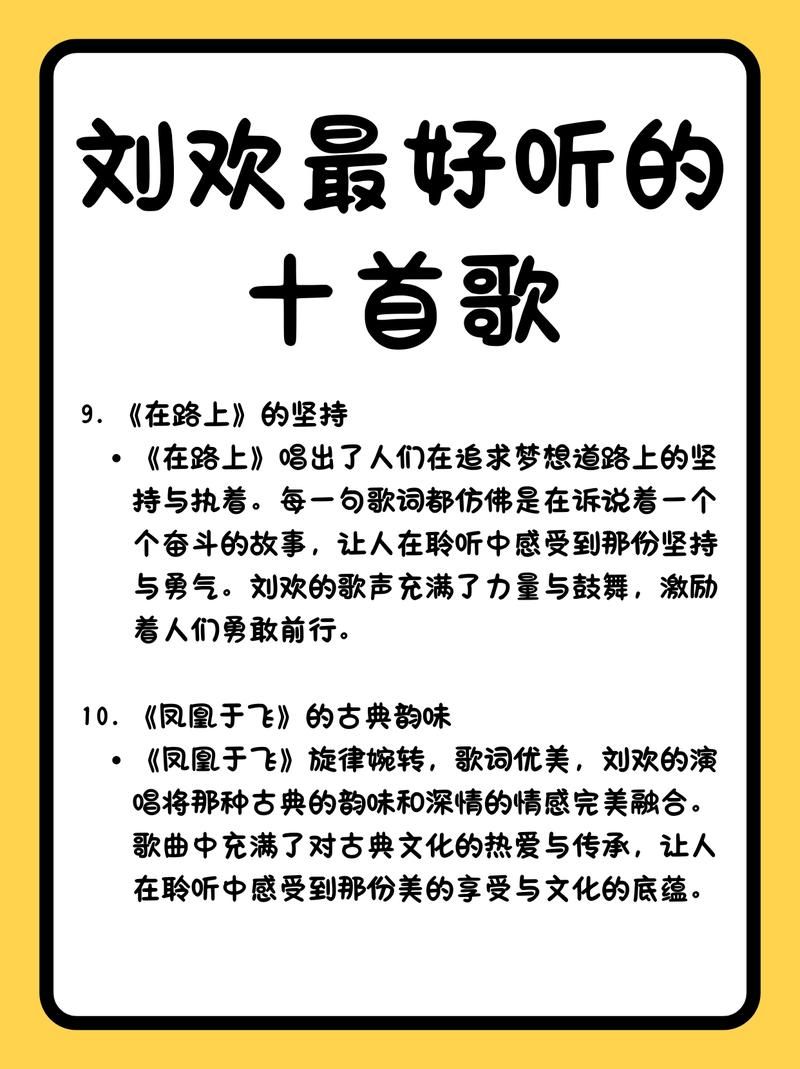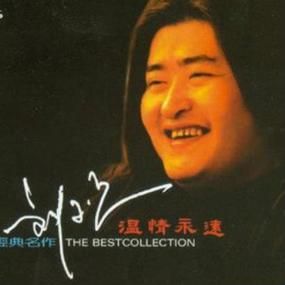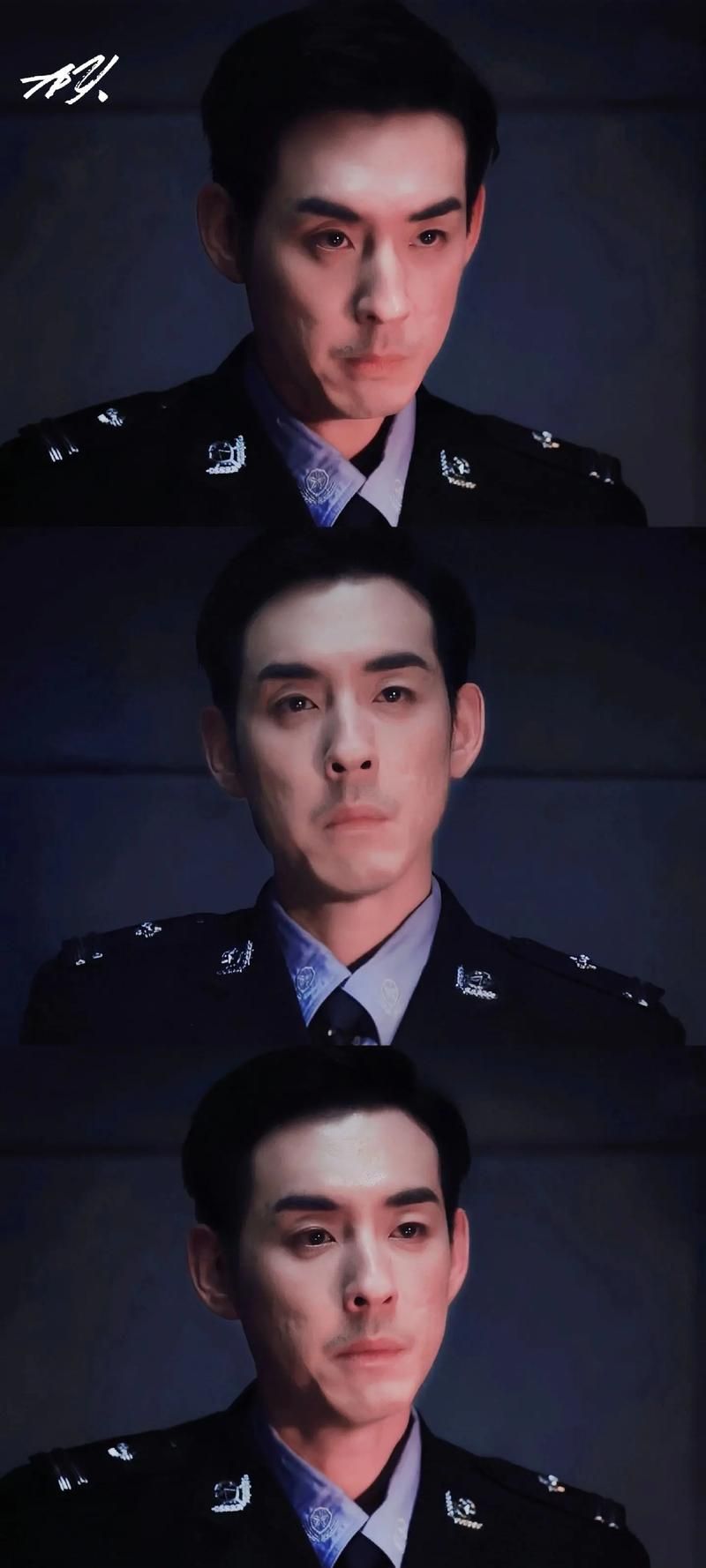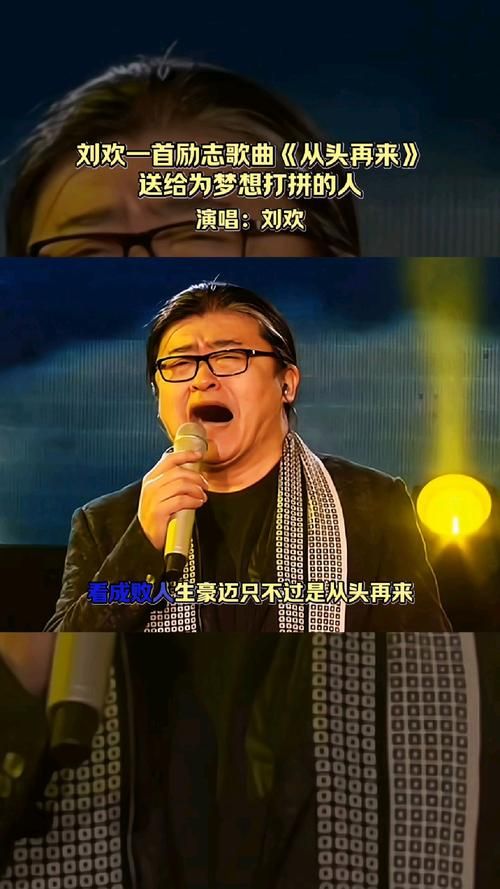那天下午,淄博张店区实验中学的梧桐树下,正飘着学生们不成调的合唱声。教音乐的王老师刚想开口纠正,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楼角转出来——黑框眼镜,洗得发白的牛仔裤,手里拎着个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旧布袋,正抬头看他们笑。有眼尖的学生小声嘀咕:“那……那不是刘欢老师吗?”

“歌王”的“意外”到访
很多人认识刘欢,是从好汉歌的“大河向东流”开始的。后来他成了歌手里的“导师”,总戴顶帽子,说话时眼睛弯弯的,点评时既犀利又带着股长辈的温和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私下里的他,最怕被叫“歌王”“艺术家”,总说“我就是个教书的,唱歌是糊口的本事”。

这次来张店区实验中学,他没提前打招呼,连淄博本地的工作人员都觉得“刘老师想悄悄看看”。事情要从一个月前说起:张店区实验中学的合唱团在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拿了金奖,校长在朋友圈发了段视频,配文是“孩子们的歌声里有光”。刘刷朋友圈时正好看见,点开听了一遍,视频里孩子们唱的是送别,有个小男孩高音破了个音,但眼睛亮得像星星。他在底下评论:“这声音干净,比录音棚里修出来的好听。”
没想到校长第二天就打来电话,说刘老师想来看看孩子们。团队劝他“随便安排个学校看看得了”,他却说“就按视频里那个操场,孩子们在哪儿唱,我就在哪儿听”。

梧桐树下的“音乐课”
那天合唱团的孩子们正排练新曲我和我的祖国,主唱是个叫小雅的女生,平时敢唱独唱,可看见真人站在台下,声线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。刘欢没坐主席台,搬了把塑料凳坐在学生队伍跟王老师一起打拍子。
“唱得不错,”他开口时声音比平时低,生怕吓着孩子们,“就是这儿,”他指了指谱子,“‘我和我的祖国’这句,‘祖国’两个字别太用力,像跟妈妈说话那样,轻轻的,心里有就行。”
小雅愣住了,电视上的刘老师点评时多严肃啊,眼前这个“戴眼镜的叔叔”却蹲下来,手指着谱子问她:“你觉得妈妈平时跟你说话,是大声喊,还是轻轻讲?”她小声说“轻轻的”,刘欢笑起来:“对呀,祖国就像妈妈,你心里爱她,不用喊出来,大家都能听见。”
他还教孩子们“用耳朵听别人”,合唱不是谁的声音大谁赢,“就像我们班,有人高有人矮,站在一起才叫全班对不对?唱歌也一样,你听她唱低音,他唱高音,合在一起,才是我们的歌。”排练到结束时,那首送别又被唱了一遍,小男孩的高音还是没完全稳,但刘欢带头鼓了掌:“今天这声破得值,比上次有劲儿多了。”
为什么是“张店区实验”?
好多人问刘欢:“您怎么想起来淄博了?”他总是摸着布袋说:“因为人家孩子唱得好啊。”但这话只说了一半。
王老师后来偷偷告诉我们,刘欢来之前,查过这个学校——张店区实验中学是所普通中学,学生大多是周边街道的孩子,不少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。合唱团是王老师带着“捡”来的器材,孩子们放学后在废弃的音乐教室练声,冬天没暖气,大家裹着羽绒服唱歌。“视频里的声音,是冻出来的。”刘欢说,“那种干净,不是教出来的,是孩子心里没杂质。”
那天走之前,他拉着校长的手说:“给孩子们弄个像样的合唱室吧,别让好声音冻着了。”后来才知道,他默默捐了一笔钱,足够给音乐教室装空调、买新谱架。但这件事,是他离开三天后,当地记者采访时,校长才“漏”出来的消息。刘欢知道了,只打电话说了句:“别宣传,让孩子们安安静安唱歌。”
艺术家,就该是“走进人群”的光
这些年,刘欢参加不少节目,也做不少公益,但像这次这样“悄悄出现”的“偶遇”,早不是第一次。他曾跑到贵州山区的村里,跟孩子们一起唱山歌好比春江水;也曾在社区养老院,听老人唱黄土高坡,然后即兴弹了段钢琴伴奏。
有人说他是“过气歌手”,可他却说:“我没想过火,就想做个能把音乐传出去的人。”在他看来,艺术不是舞台上的灯光,“是老百姓嘴里哼的小调,是孩子们跑调的合唱,是菜市场里吆喝的调子——这些都藏着真东西。艺术家得去听这些,不能只待在录音棚里。”
淄博的这场相遇,没有热搜,没有红毯,甚至连张照片都是学生偷拍的。但王老师后来发了一条朋友圈,配图是学生们在新装好的空调房里唱歌,文字写着:“今天的风是甜的,因为刘欢老师说,‘好声音值得被温柔对待’。”
其实我们总在问:明星的意义是什么?是舞台上的光鲜,还是作品中的才华?或许刘欢用这次“意外”的到访告诉了我们——真正的艺术家,心里装着土地的温度,耳朵听得见普通人的声音,手里握着把能“把人聚在一起”的琴。就像那天张店区实验中学的梧桐树下,没有聚光灯,只有孩子们的歌声和那个戴眼镜的男人,在轻轻点头说:“真好听,再唱一遍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