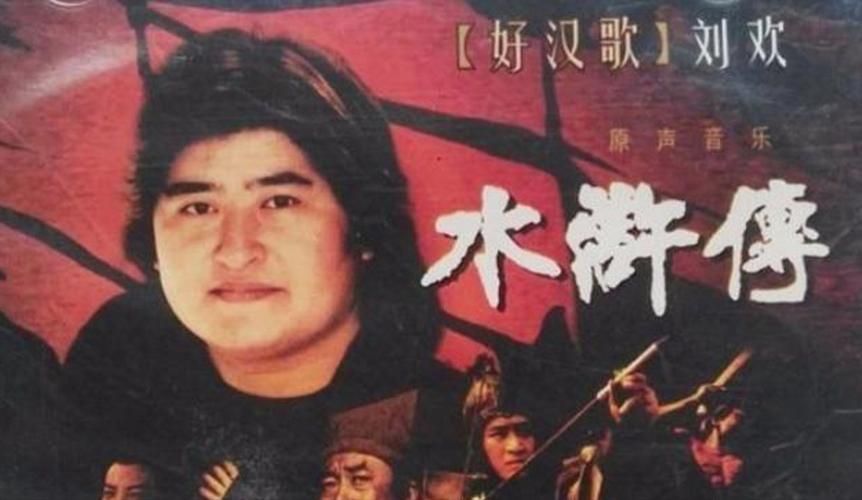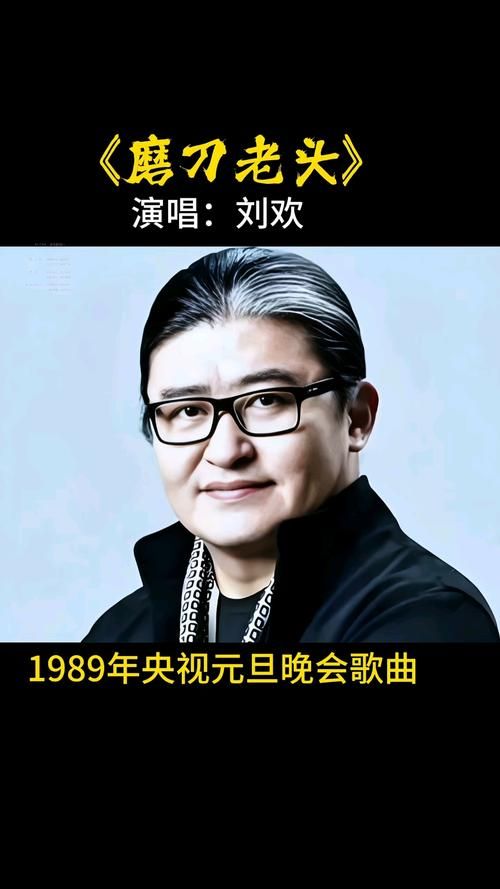前几天深夜刷到一个视频,差点没忍住喊出声来。镜头里,刘欢穿着件简单的黑色毛衣,坐在录音棚的钢琴前,面前摊开一幅泛黄的油画——画上是群山连绵,江水流淌,几叶小舟漂在江面,远处的亭台楼阁被云雾半遮半掩。他盯着画看了足足五分钟,手指悬在琴键上,像在跟画“对话”,突然指尖落下,一段带着古韵又藏着现代感的旋律就流淌了出来。更绝的是,他旁边放着支毛笔,弹到高潮时竟拿起毛笔,跟着节奏在旁边的宣纸上随手勾勒两笔,笔锋起落间,画里的山水仿佛真的“动”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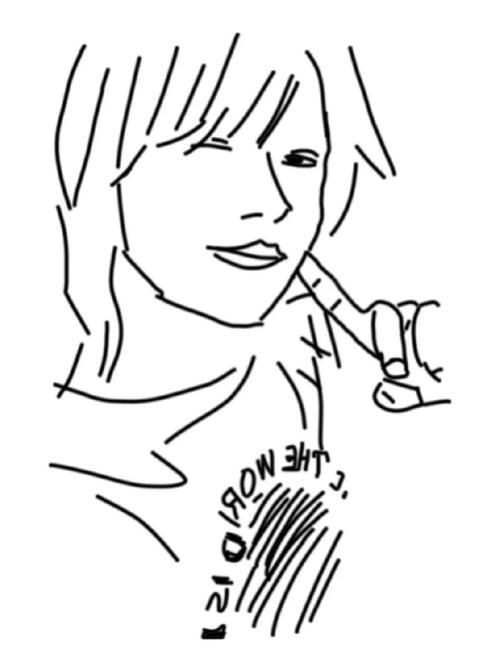
评论区炸了:“这哪是改编画?这是让画开口唱歌啊!”“从小听刘欢的歌,没想到他还会‘画’音乐?”有人甚至翻出三十年前他唱好汉歌时的视频,对比着说:“你看他当年唱‘大河向东流’,眼神里就有山水,现在直接把‘山水’搬到琴键上了。”
一、不是所有改编都叫“刘欢改编”:他先把画“读”透了

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刘欢这次“改编画”的契机,其实挺偶然。前阵子他参加一个艺术跨界节目,导演组请他用音乐诠释一幅明代古画千里江山图的局部。制片人一开始还担心:“刘老师,这画里的青绿山水,怎么用音乐表现啊?是用电钢琴还是加民族乐器?”
他摆摆手:“先别急着谈乐器,你把这幅画的历史背景讲给我听。”那两天,他拉着节目组的历史顾问,从画作者王希孟的生平聊到宋代文人画的“可游可居”——从18岁少年画完这幅画就英年早逝的遗憾,到石青、石绿颜料要经12遍烘染的匠心,再到画中那些“可行、可望、可游、可居”的亭台楼阁,仿佛自己真的走进了画里。
“你知道吗?”后来他对镜头说,“你看着画里的那条江,会想到它可能流过诗人李白的‘轻舟已过万重山’,也可能流过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’。音乐不是凭空编出来的,你得先懂画里藏着多少故事。”
所以当第一段旋律从他指尖出来时,没人觉得突兀:开头是古筝的轮指,像江水轻轻拍岸,接着大提琴低沉地响起,像是山在回应,然后钢琴高音区突然跳出一个清亮的音符——那是画里被云雾遮住的飞檐,阳光突然照进来的感觉。
二、“用音乐画出线条”:他的改编从来不止“好听”
有人可能会问:“不就是给画配个背景音乐吗?哪有那么神?”
但看过刘欢现场改编的人都知道,他的“改编画”从来不是简单的“音画配合”,而是把画拆解成“音乐元素”,再重新“组装”成一首新歌。
上次改编那幅富春山居图时,他盯着画里的“坡石技法”愣了半天——黄公望用披麻皴画出的山石纹理,线条时而细腻时而粗犷,怎么用音乐表现?最后他想了个办法:用笛子的滑音模仿线条的“走势”,用钢琴的强弱变化表现皴法的“浓淡”。最绝的是,他让歌手模仿画中樵夫的吆喝声,那种带着山野回响的“嘿呦”,一下子就把人拉进了画里的场景。
“你以为他只是在弹琴?不,他是在用音乐‘画’线条。”节目组的编曲师后来采访说,“有一段我卡住了,觉得音阶怎么都不对,他指着画说:‘你看山石的这条边,是不是有个小小的顿挫?音阶这里加个半音,就像笔尖稍微提了一下。’”
结果那段旋律出来,导演组当场掉眼泪:“我好像真的看到黄公望拿起笔,在纸上画出了那个顿笔。”
三、为什么是刘欢?因为他懂“艺术都是通的”
其实娱乐圈里“跨界”的明星不少,但能把“画改编成音乐”做出境界的,掰着手指头数可能也就刘欢。有人说,这是因为他“有音乐天赋”,但更根本的原因,或许是他骨子里对“艺术本源”的尊重——在他眼里,音乐、绘画、文学,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:用一种形式,表达对世界和生命的理解。
他曾在采访里说:“我年轻的时候觉得音乐是最好的,后来慢慢发现,一首唐诗里有画的意境,一幅画里有诗的韵律。你读‘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’,脑子里不就自动出现画了吗?那反过来,画能不能变成诗,诗再变成歌?”
这次改编画的时候,他特意找来画家朋友听成品,画家听完说:“你的音乐里,有我调颜料时的感觉——‘石绿’和‘花青’混合时那种微妙的色彩变化,居然用钢琴的泛音表现出来了。”
这种“打通艺术壁垒”的能力,才是他最厉害的地方。他不是在“炫技”,而是在告诉所有人:艺术没有高低之分,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沉下心,去懂另一种语言。
四、比起“成功”,他更怕“套路”
有人可能会问:“刘欢老师现在功成名就了,为什么还要做这么‘吃力不讨好’的事?”
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做“跨界改编”。早在十几年前,他就把古琴曲梅花三弄改编成交响乐,把四川清音放进流行歌曲;疫情期间,他闭关三个月研究京剧的“西皮流水”,最后写出一首融合京剧和老摇滚的歌。
“有人说我‘没事找事’,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觉得累吗?”他说,“每次接触新的艺术形式,都像打开一扇新的大门。你看着画里的山水,会突然想到‘原来江水的声音是这样的’;你听着戏曲的唱腔,会明白‘原来喜悦的情绪可以这样表达’。这些东西,是你在录音棚里重复一百遍老歌也体会不到的。”
他最怕的,是“重复”——重复自己,也重复别人。“现在太多歌听起来都一个样,和弦进行一样,歌词套路一样,那不行。艺术得不断‘破’,才能不断‘立’。”
写在最后:艺术最好的样子,就是“让万物说话”
前几天,那个“刘欢改编画”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平台火了,很多外国网友留言:“这是什么魔法?我从没想过画会唱歌!”“我现在要去博物馆看画了,因为我想知道它们会‘唱’什么歌。”
突然想起刘欢在节目最后说的话:“我们总说艺术是给人享受的,但我更觉得,艺术是让万物都能‘说话’。你看这幅画,它不会说话,但懂它的人能听到它的声音;音乐也不会说话,但懂它的人能看见它的画面。而我们要做的,就是做那个‘翻译者’。”
是啊,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到弯弯的月亮,从好汉歌到现在的“改编画”,刘欢好像一直在做一件事:用不同的语言,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——只要用心,万物都会唱歌。
下次当你站在一幅画前,别急着拍照发朋友圈,不妨站一会儿——说不定,你会听到刘欢听到的那个旋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