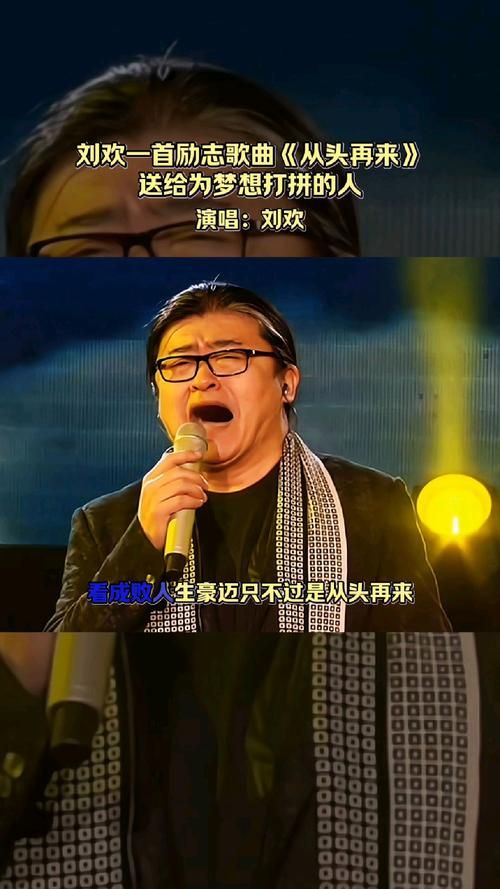翻开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欢的课程表,你会发现没有“明星光环”这四个字,却有“凌晨五点的备课笔记”“磨破三副白手套的示范教学”,还有那句被学生传了十年的课堂开场白:“今天我们不聊技巧,先聊聊音乐里‘人’的温度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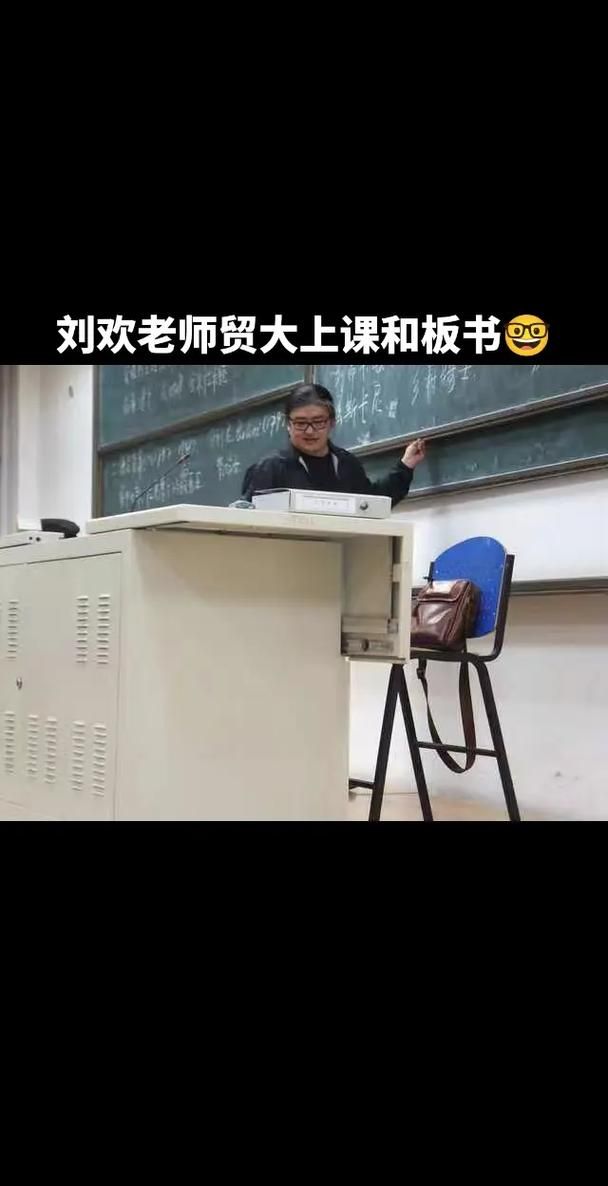
从演唱会舞台到三尺讲台:他带着“笨办法”来了
2017年刘欢正式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科技系教授,彼时他刚结束中国好声音导师工作,手握金曲奖、格莱美提名,却没在第一堂课炫技,而是抱着一摞泛黄的磁带走进教室。“这是我大学时录的 demo,你们听听跑调了多少处。”磁带沙沙转动里,是他22岁在校时参加校园歌手比赛的录音,破音、抢拍,甚至紧张到忘词咳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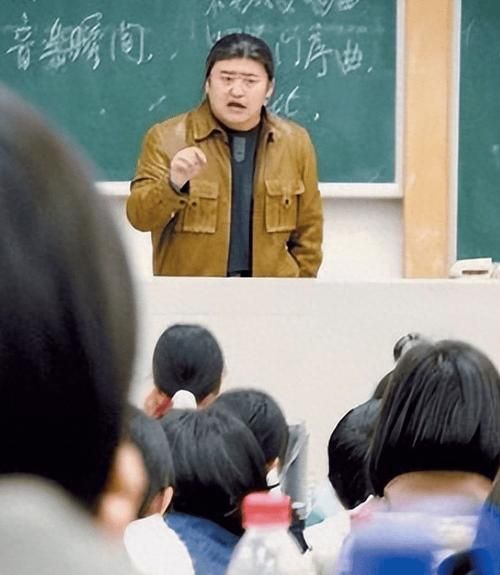
“我年轻时觉得嗓子是天赐的礼物,直到遇见恩师才懂,嗓子只是工具,‘人’才是音乐的灵魂。”刘欢坐在堆满乐谱的办公桌前,指尖划过学生作业上的批注——这页纸密密麻麻写满修改建议,不同颜色的笔迹标注着气息控制点、“情感爆发前的留白逻辑”,甚至有他用铅笔画的“心跳频率图谱”。有学生偷偷拍下作业照片发在社交平台,配文:“刘老师改作业比追剧还认真,每个音符都是‘活’的。”
教他唱歌,不如教他“如何当一个歌者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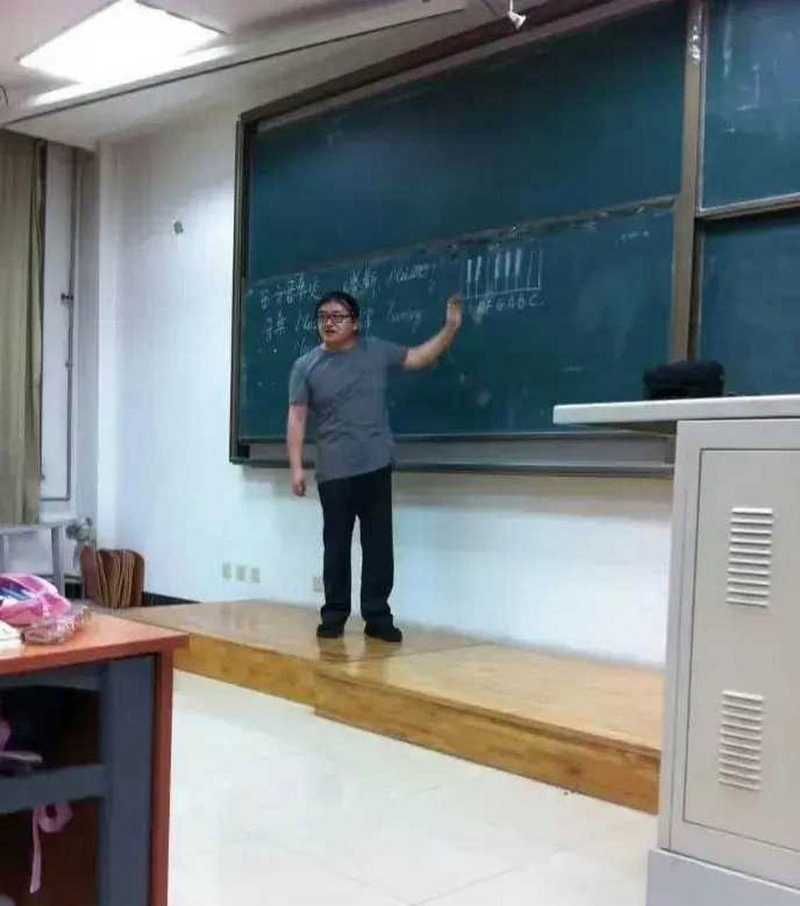
“你们有没有唱到累得发抖,却觉得没唱对的时候?”在某节声乐课上,刘欢突然问台下的00后学生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他没有纠正发声方法,而是打开手机播放了一段阿黛拉Live版的Rolling in the Deep:“听她第三句气口前的那个哽咽,不是技巧,是想起和前任分手的那天雨有多大。”
在他的课堂上,解剖学、心理学、甚至哲学都是必修课。他会带着学生分析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如何用和声变化表现“从绝望到希望”,也让学生给校园里的保洁员写首歌,“别用华丽辞藻,写写她扫落叶时手腕的弧度”。有学生写了一首关于宿管阿姨的民谣,旋律简单却催人泪下,刘欢在评语里写:“音乐不是用来‘震’人的,是用来‘接’人的——接住那些藏在生活褶皱里的情绪。”
最“不务正业”的教师,最“有用”的课
刘欢的课从不点名,却从没有人早退。有学生为了抢前排,凌晨六点就去教室门口排队;有毕业生发消息说:“刘老师教我用歌声安慰失恋的朋友,现在我用这方法安慰情绪崩溃的同事。”更“离谱”的是,他会带着学生去菜市场听小贩的吆喝,在地铁里收集报站声回来做采样,“好音乐不在剧院里,在日日走过的烟火人间里”。
去年冬天,他带着学生排演我和我的祖国,当一名平时说话都脸红的女生唱到“我最亲爱的祖国”时突然破音,台下安静了三秒,接着响起掌声。刘欢走上前递过纸巾,笑着说:“破音好啊,证明你是真唱——真情实感,永远不怕跑调。”
结语:当明星光环褪去,留下的是什么?
如今刘欢依旧活跃在舞台,但他更常被学生提起的,是那个冬天他为生病学生请假、亲自去家里补课的身影,是他在走廊里听见有人哼跑调,会走过去轻声说“这里试试把喉咙松一松”,是他写在课程大纲最后一行的话:“别成为‘唱歌的机器’,要成为‘有血有肉的歌者’。”
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:刘欢站在讲台前,除了歌声还能给学生带来什么?大概是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,是“人比技巧更重要”的坚守,是那句“你只管用心,剩下的交给时间”的底气。毕竟,能把“教唱歌”变成“教做人”的老师,本就是舞台之外最动人的旋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