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夜的录音棚里,键盘手刚弹完一段旋律,坐在控制台前的刘欢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。“这段编曲虽然时髦,但少了点地域文化的‘根’——你们听,新疆十二木卡姆的节奏型藏在里面,像不像沙丘里藏着的河流?”她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波形图,眼睛里的光比台灯还亮。
这不是普通音乐制作人的点评,因为她名片上的头衔除了“资深音乐制作人”,还有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博士”。在“流量为王”“快餐创作”当道的娱乐圈,这样一个带着学术标签的人闯进来,像往沸腾的火锅里扔了一块冰——有人好奇:博士懂市场吗?她的研究能给明星写歌、帮综艺攒局带来什么?也有人质疑:学术和娱乐,本来就是两条平行线,硬凑着有意思吗?
从教室到录音棚:博士的“田野调查”是去娱乐圈“采风”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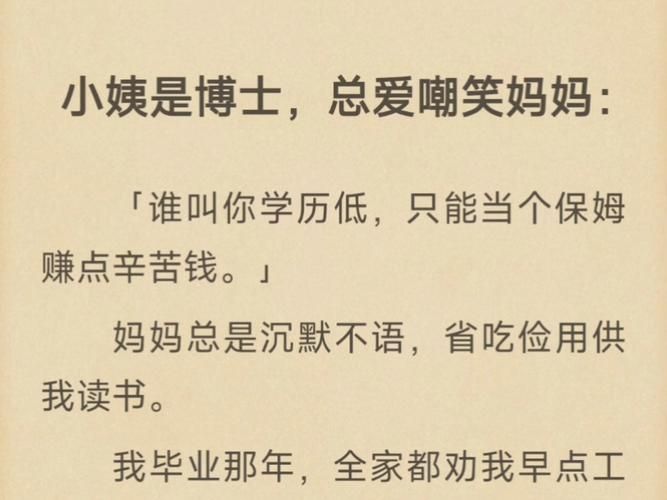
“很多人以为音乐人类学就是‘研究音乐的历史’,其实不然。”刘欢婷在一次论坛上解释,她的研究方向是“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符号建构”,简单说,就是“流行歌为什么能火,火背后藏着什么社会情绪”。
为了搞懂这个,她的“田野调查”地点有点特别。别人做人类学去偏远村落,她扎进选秀后台、综艺录制现场,甚至跟着流量明星的粉丝团蹲点。“有次录歌手,我连续三周待在待机室,不是看歌手排练,是观察他们候场时听什么歌、化妆师聊什么、粉丝应援口号怎么变。”她笑着递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,里面贴着演唱会票根、粉丝手绘,还有密密麻麻的——“某明星候场循环孤勇者,因歌词‘战吗?战啊!’与粉丝‘打投’情绪共振;某综艺剪辑时刻意放大素人弹唱‘乡愁’片段,引发都市群体共鸣。”
这些“接地气”的观察,成了她学术研究和商业实践的“中间键”。去年,她为一位转型演员的歌手写歌,没有写情情爱爱,而是基于她调研的“Z世代职场焦虑”,融合了电子音乐和传统戏曲念白,歌名不卷行不行上线后,不仅登顶音乐平台热歌榜,还被多家媒体评为“年度社会观察歌曲”。“很多人说博士写歌‘太有深度’,但恰恰相反,我研究的是‘人的真实情绪’,这才是流行音乐最该有的根。”她对着电脑,屏幕上是即将发布的综艺主题曲,备注写着“今晚和95后实习生聊了聊,他们觉得‘躺平’是玩笑,其实是‘累了的坚持’,这首歌得把这个劲儿写出来。”
她不是“圈外人”,是给娱乐圈“搭桥”的人
在娱乐圈,“跨界”不少,但“学术+娱乐”的跨界,刘欢婷可能是做得最“轴”的一个。有次,她接到某网综邀约,做“传统文化音乐改编”的导师,节目组希望她多加点“网红乐器”“电子remix”博眼球,她却坚持先带着团队去云南采风,学了几个月的彝族月琴和酒歌。“不是排斥流行,而是‘改编’不是‘拼凑’。”她在节目里拿着月琴说,“彝族老乡弹小苹果调子,他们听着像笑话,因为月琴的‘魂’是‘情歌对唱’时的对话感,没了这个,再热闹也是空的。”
这档节目后来拿下了“年度文化传播综艺奖”,很多观众留言:“原来非遗音乐这么好听,不是老头老太太的专属。”刘欢婷说,这让她更坚信:“学术不是高高在上的,娱乐圈也不是浅薄的,把两者打通,能让好内容‘既有温度,又有深度’。”
现在,她手下既有刚出道的新人歌手,也有一线制作公司,合作项目从电影配乐到偶像男团主打歌,但所有项目都有个共同点:必须先过“文化价值关”。“有次投资人说找首‘抖音神曲’,数据肯定火,但歌词是‘哥哥妹妹亲亲我’,我直接拒绝了。”她语气软但立场硬,“音乐可以娱乐,但不能‘娱乐至死’,尤其对影响年轻人的内容,我得守住那条线——这不是说教,是责任。”
娱乐圈需要“刘欢婷们”吗?
采访快结束时,有工作人员跑过来说:“欢婷老师,那个说要做‘国风摇滚’的乐队,拿着您给他们列的‘宋词韵脚表’改词呢,说比之前顺耳多了!”她笑着摆摆手,眼睛里的光又亮了。
有人说,刘欢婷像娱乐圈里的“啄木鸟”,专挑“内容空心化”的毛病;也有人觉得,她把学术弄得太“重”,娱乐就该轻轻松松。但看着她录音棚里堆着的“音乐人类学论文集”和“偶像打歌榜”,突然觉得,或许娱乐圈正需要这样“不务正业”的人——不是所有人都该追流量,但总得有人,愿意花时间去研究“为什么一首歌能让人听了哭”,去守护“内容比数据更重要”的底线。
那么,当越来越多的“博士”“学者”走进娱乐圈,是会让这个圈子变得更“有料”,还是会变得太“端着”?刘欢婷没直接回答,只是打开手机,放了她刚帮一位农民工写的歌——城市里的月亮。“你看,他唱‘工地的钢筋比月亮硬,但思念比钢筋弯’,这就是最好的答案。”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