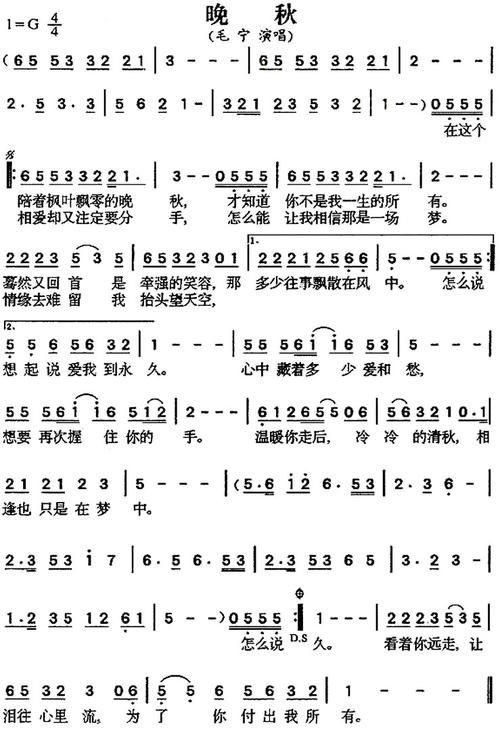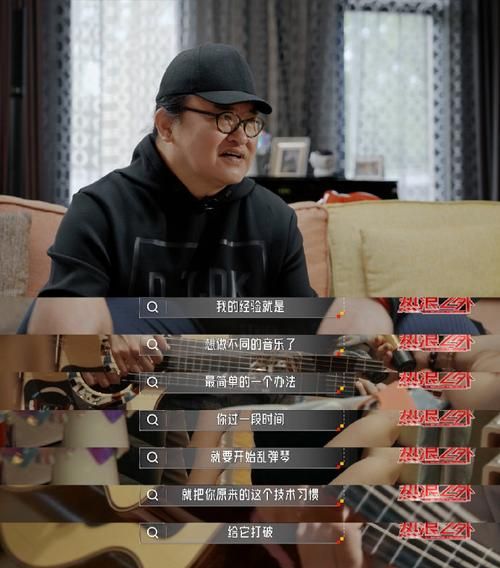2019年,歌手总决赛的舞台上,刘唱完弯弯的月亮后对着镜头笑了笑,说:“以前总觉得‘在路上’是出发,现在才发现,其实‘在路上’是‘还在走’。”
那时他刚做完手术一年,体重从190斤掉到130斤,穿以前演出服要塞三个枕头,唱高音得比划着打拍子给自己找节奏。可镜头扫过观众席,前排有人举着“刘欢,我们等你回来”的灯牌,他突然红了眼眶——是啊,从1987年首都高校英语演唱比赛夺冠,到2023年为流浪地球2唱人是-,这条路他已经走了整整36年。
“歌坛常青树”不是天生的,是“走”出来的

很多人对刘欢的初印象,是北京人在纽约里那首千万次的问:“千万里,千万里,我追寻着你……”1993年,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,但少有人知道,为了录好这段高亢又深情的旋律,刘欢在录音棚里熬了三个通宵。
“当时录音棚的空调坏了,他裹着大衣唱,嗓子哑了就用冰块含着,含完接着来。”后来导演郑晓龙回忆,录到副歌时刘欢突然吼出一嗓子,整个棚的人都起鸡皮疙瘩——那是真正用生命在唱歌的劲儿。
这种“劲儿”一直持续着。90年代的他,是内地歌坛的“顶流”,唱片销量破百万,春晚舞台上的相约一九九八和那英成为经典,可他却在事业最顶峰时跑去美国深造音乐硕士。有人问他“放着钱不赚去读书图啥”,他挠挠头:“总觉得嗓子能唱的日子有限,得赶紧多学点,不然以后唱不动了拿什么吃饭?”
回国后他没急着翻红,而是一头扎进大学课堂,教流行演唱、开大师课,把从国外学到的“气息控制”“情感共鸣”掰碎了讲给学生。学生说他“上课从不端着,会笑着听我们跑调,然后蹲下来在钢琴上比划‘这里气息要沉下去’”;同事说他“把名利看得很淡,有次节目组想给他加片酬,他摆摆手:‘把钱省给年轻编曲师吧’”。
原来“在路上”不是非要狂奔,有时候是慢慢走,是愿意停下来,为别人铺一段路。
“病痛拦不住我,顶多就是换种走法”
2018年,刘欢被确诊患上“股骨头坏死”,必须尽快手术。医生说:“以后不能长时间站立,唱歌也得控制。”他听完沉默了半晌,突然问:“那我能坐着唱吗?”
手术后那两年,他几乎“消失”在公众视野。直到2019年接到歌手的邀约,妻子卢璐劝他:“你身体还虚,别折腾了。”他指着手机里存的歌单说:“你看,这首歌我准备了两年,就想着能在舞台上唱一次。”
舞台上的他,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:唱从前慢时右手会不自觉地扶着腰,唱夜时中间要歇两口气,可每当他开口,那熟悉的醇厚嗓音还是会让人瞬间共情。那季比赛他拿了亚军,领奖时他说:“以前总觉得‘赢’很重要,现在发现,能站在这里,把歌唱给大家听,就是赢了。”
康复的日子里,他爱上了“走”的另一层含义——慢慢走。每天在家附近的公园散步,看着晨练的老人打太极、小朋友追着跑,他会拿出手机录下来,配上小调发到朋友圈:“今天的风是F调的,适合散步。”有粉丝评论:“刘老师,您的歌声像春天的风。”他回了个笑脸:“你们的陪伴,就是风里的暖。”
“最好的‘在路上’,是带着初心往下走”
这几年,很多人问刘欢:“早就不缺名利的您,为什么还那么拼?”
他想起2008年汶川地震时,连夜赶录因为有你,嗓子唱出血丝也没停;想起2019年为流浪地球写人是-,和导演郭帆讨论“带着地球去流浪”的哲学,琢磨着“‘流浪’不是失去,是带着家一直往前走”的那种倔强。
“就像我父亲说的,”有次采访他提到去世的父亲,“人这辈子就像走一条没头的路,重要的不是走到哪儿,而是心里揣着火——对音乐的火,对生活的火,对人的火。这火不灭,就能一直走下去。”
如今的刘欢,很少参加综艺了,更多时间是在家作曲、陪女儿练琴,或者在学校的课堂上给学生们讲“怎么用声音讲故事”。有人说他“退圈了”,可我们知道:只要他一开口唱“千万次的问”,只要他还在课堂上说“唱歌要用心”,他就从未停下“在路上”的脚步。
36年前,21岁的刘欢站在高校比赛的舞台上,眼里是“要去远方”的光;36年后,57岁的他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手里捧着老伴泡的茶,嘴角是“走了这么久,挺好”的笑。
或许,“在路上”从来不是非要抵达某个终点,而是在每一次出发、每一次坚持、每一次停下后重新出发里,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——像刘欢那样,带着歌声,带着初心,一直“走”下去,直到成为别人路边的光。
毕竟,真正的“在路上”,从来不怕慢,只怕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