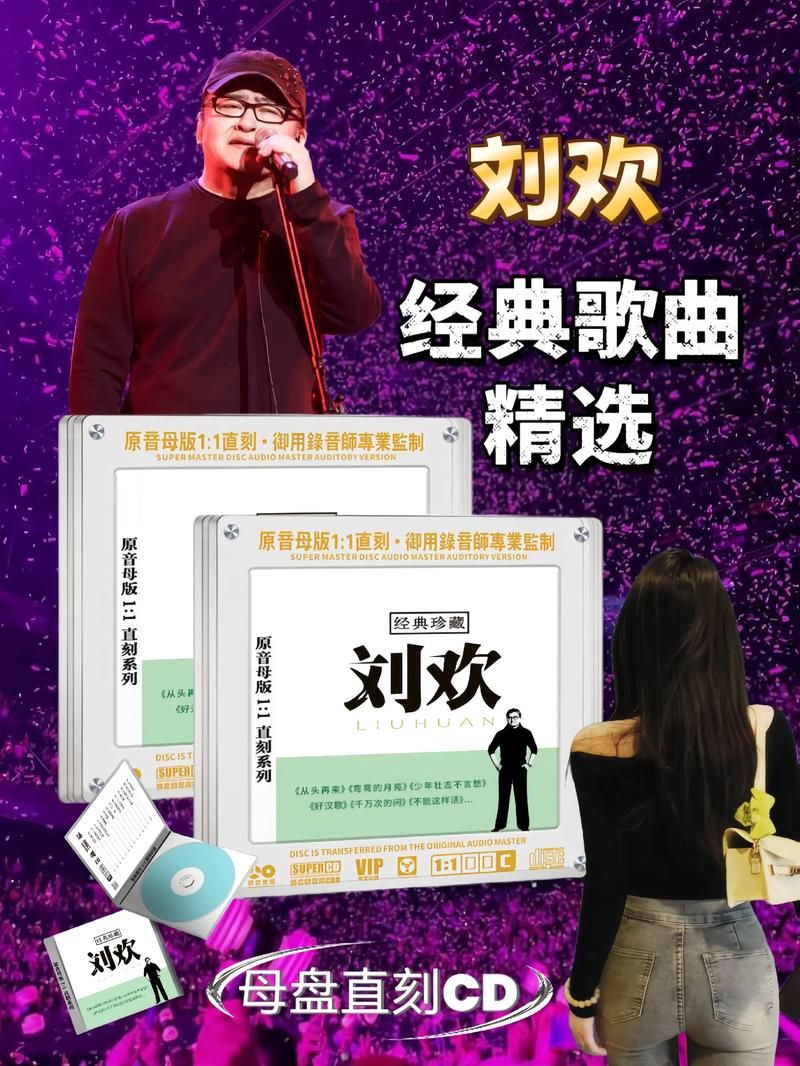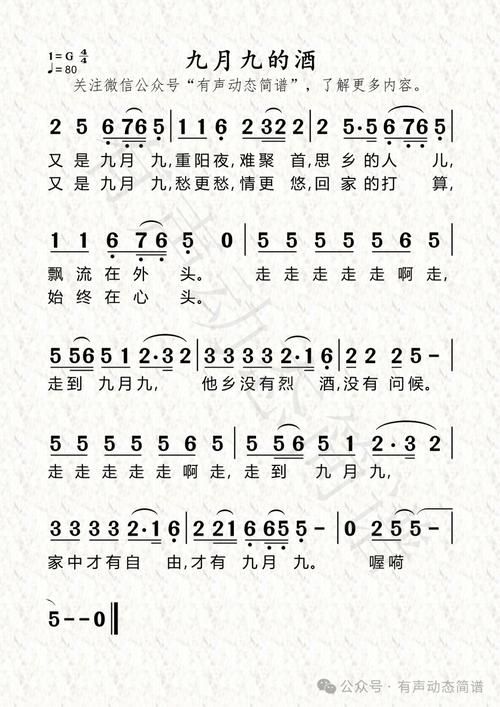九月的中午,阳光把郑州中牟某中学的走廊晒得发烫。高二(3)班的语文课上,刘欢抱着教案刚走进教室,后排就有男生起哄:“欢姐,今天讲不唱少年中国说啊?”

她笑着白了一眼:“想得美,先默写。”却在转身板书的瞬间,悄悄从教案里抽出一沓彩色的“诗词卡”——正面是“大江东去”,背面是“苏轼这辈子,可不止是个词人”。
这个场景被学生偷偷拍下来,发到网上时,没人想到会掀起一场“追老师的狂潮”:一周内,她的课堂视频播放量破2000万,“中牟教师刘欢”冲上同城热搜第一,甚至有外地家长特意带着孩子来学校“蹭课”,只为“看看能让眼睛发亮的语文课到底长什么样”。

她不是“网红”,只是个“想把讲台唱活的”普通老师
其实刘欢自己都没想到,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课堂尝试,会被这么多人看见。
教语文十二年,她一直记得刚入职时老校长说的话:“语文不是死记硬背,是要让文字长出脚,走到学生心里去。”于是她的课堂,总有“意料之外的小花样”。
讲孔雀东南飞,她会提前让学生分组排话剧,自己熬到凌晨做道具——焦仲卿的官服是用旧床单改的,刘兰芝的裙裾缀着亮片,连“孔雀”的头冠都是用彩纸糊的,上台时羽毛被风扇吹得乱飞,底下学生笑得前仰后合,却后来能把“君当作磐石,妾当作蒲苇”背得一字不差;
讲现代诗雨巷,她特意选了个阴雨天,带着学生撑伞走到操场,让他们“真的闻一闻丁香一样的忧愁”,有个男生后来写周记:“原来‘凄清又惆怅’不是课本上的词,是雨水打在伞上的声音”;
甚至讲到鲁迅的故乡,她会在黑板上画一幅“闰土月下刺猹”的简笔画,配着河南话的旁白,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月亮,下面是海边的沙地,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……”
“有人说我是‘网红’,可我每天想的,就是怎么让学生盼着下一节语文课。”刘欢对着整理采访提纲的笔记本笑了笑,指尖沾着点粉笔灰,“比起点赞量,我更在意那些下课围过来说‘老师,我昨天看诗了’的学生。”
从县城课堂到全网热搜:“好老师”从来不需要“滤镜”
刘欢的走红,其实藏着时代对教育最朴素的期待。
有网友翻出她早年的朋友圈:2019年冬天,她在深夜给学生发消息“作文改完了,明天来找我拿,不冷”;2021年春天,她带着留守儿童去公园放风筝,配文“看到他们笑,觉得风都是甜的”;甚至还有学生分享的聊天记录——“老师,我数学考砸了,还能学好语文吗?”“当然能,文字里藏着你没发现的勇气。”
这些零散的片段拼凑出一个真实的刘欢:会为学生的进步偷偷抹眼泪,会和家长打电话聊到手机发烫,会在学生情绪低落时,塞给他们一颗糖和一张写着“没关系,再来”的卡片。
就像她在采访里说的:“我不是什么‘完美老师’,也会发脾气,也会觉得累。但我永远记得,我面对的不是‘考生’,是活生生的人——他们需要被看见,需要被鼓励,需要知道,学语文不只是为了考试,是为了有一天能看清自己的心,也能读懂别人的故事。”
当“讲台流量”遇见“教育初心”:我们究竟在追什么?
刘欢火了之后,网上有人讨论:“县城老师走红,是不是教育的‘流量密码’?”
但真正看过她的课堂就会发现,哪里有什么“密码”,不过是把学生放在心上罢了。她会在备课时琢磨“00后爱听什么”,把RAP改编成古诗赏析;会记得每个学生的生日,在黑板角落画个小蛋糕;甚至会在讲台上放一个“烦恼回收箱”,让学生匿名写下压力,她每天抽几个“开解”。
这些事,没有惊天动地,却藏着教育最本质的样子——用真心换真心,用热爱点燃热爱。
就像那个特地从洛阳赶来的家长说的:“我女儿以前不爱学语文,说‘古文像天书’。看了刘欢老师的视频,她主动把蜀道难背下来了,还说‘妈妈,原来李白这么酷’。我们要追的,不就是这样的‘光’吗?”
夕阳把教学楼染成金色时,刘欢刚送走最后一节晚自习。走廊里,学生笑着和她挥手:“欢姐,明天见!”她挥了挥手,转身往办公室走,背影被拉得很长。
或许对很多人来说,“刘欢”不是一个名字,而是一种提醒: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总有人愿意慢下来,在平凡的讲台上,用最朴素的方式,点亮一盏又一盏灯。
而那些被点亮的灯,会照着学生走向更远的地方——就像她在课堂上常说的:“文字有力量,讲台有温度,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‘星辰大海’。”
讲台边的“顶流”,从来不该是聚光灯下的明星,而是像刘欢这样,让每个学生都觉得“被需要、被看见、被期待”的老师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