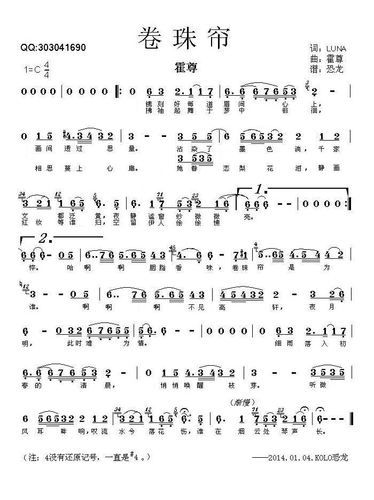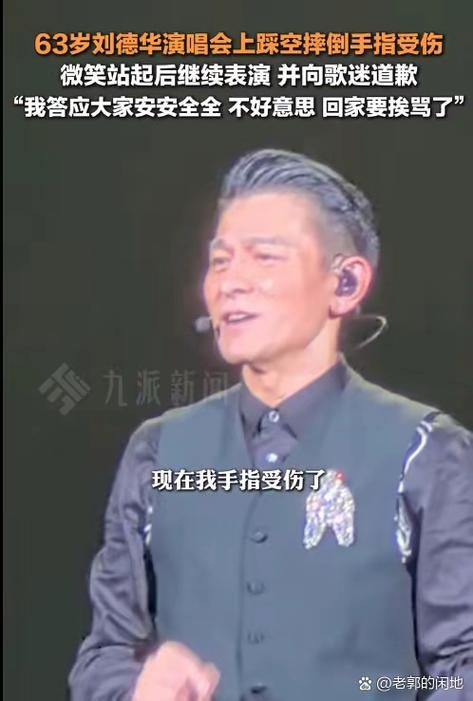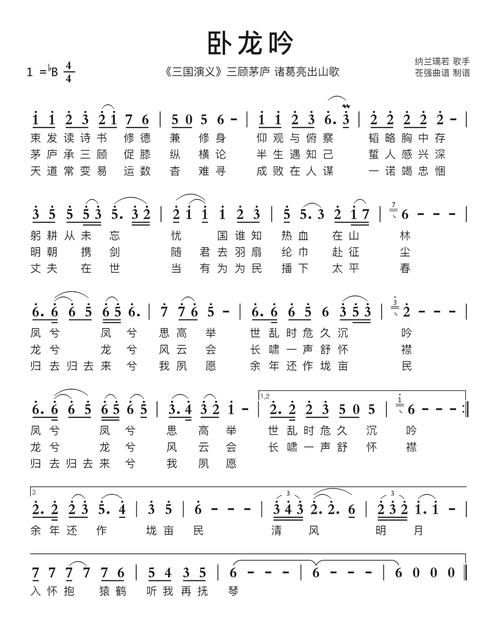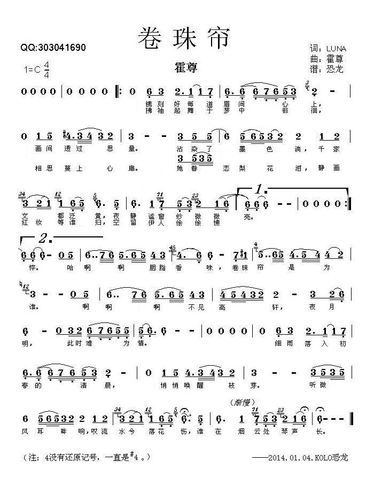清晨六点半,南昌的秋还带着点凉意,青云谱区某中学的教师公寓里,刘欢已经悄悄起了床。轻手轻脚地收拾好桌面,把昨晚备好的背影教案又翻了三遍——这是她教书的第28个年头,却依然会在第二天要上的课文旁,用红笔标出“此处要停顿,让学生想象父亲爬月台的动作”。
“刘老师的课,像听故事一样。”这是学生最常对她的评价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这个“会讲故事”的背后,是多少个深夜的灯光,和对“教育”这两个字近乎固执的较真。
从“刘老师”到“欢姐”:她把每个学生都写进了自己的故事里

1995年,22岁的刘欢踏进南昌某中学的语文课堂,那时的她还扎着马尾辫,说话带点怯生生的赣南口音。第一堂课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,她没急着分析段落大意,而是问学生:“你们有没有偷偷养过蚂蚱?有没有在夏天的夜晚听过蝉叫?”
教室里安静了三秒,突然有个男生举了手:“老师,我把蜻蜓养死了,我妈骂了我一整天。”刘笑了——她知道,课本里的文字活了。
后来,学生们爱上了她的“故事课”:讲孔乙己,她会模仿孔乙己“排出九文大钱”的姿势,逗得全班大笑;讲木兰诗,她甚至让学生分组排情景剧,有个平时调皮的男生演花父,把“愿为市鞍马”的严肃演出了哭腔,那天刘欢在备课本上记下:“每个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份柔软,只是等老师来敲门。”
2008年,班里有个叫小宇的男生,父母离异后变得沉默寡言,作业常常不交。刘欢没请家长,也没批评他,每天放学后拉着他去操场散步。“老师,我妈说我以后肯定没出息。”有天小宇突然开口。刘欢停下脚步,指着天边的晚霞:“你看那朵云,像不像你妈?她可能说过气话,但就像云飘走了,太阳还会出来。你觉得,你妈希望你一直躲着,还是希望看到你抬起头?”小宇哭了,后来他考上了一所职业高中,寄了张贺卡给刘欢:“欢姐,谢谢你当时没放弃我。”如今,小宇成了汽修师傅,过年还会给刘欢发视频,笑着喊“刘老师,我修的车,跑得可快了”。
“语文不是考点,是生活本身”:她把“分数焦虑”变成了“成长惊喜”
在不少家长眼里,刘欢是“佛系老师”——别的班都在拼命刷题,她却每周匀出一两节课带学生读诗。春天带他们去公园找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春色,秋天在操场捡梧桐叶当书签,甚至还在班里办过“豆腐文学社”,让学生把自己的生活写成故事。
“刘老师,我家孩子这次月考作文扣了10分,您能不能多讲点套路?”有家长曾急匆匆地找她。刘欢递了杯水,笑着说:“您觉得,‘我的妈妈冒着雨送我去医院’和‘我妈的雨衣上滴着水,怀里却裹着我干干的书包’,哪个更能让老师记住?”
她的学生,作文里很少有“高大上”的空话,却满是让人心头一暖的细节。有个学生在我的爸爸里写:“爸爸是修车工,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油渍。那天我问他‘你手不脏吗?’他笑着给我看拇指上的茧——‘这是攒力气养你的勋章’。”这篇作文后来被刊登在报纸上,家长专门来学校,握着刘欢的手说:“谢谢您,让孩子学会了爱。”
28年来,带过15届毕业班,她的语文平均分从未掉过年级前三,但更让她骄傲的,是毕业多年的学生还会给她发消息:“老师,我现在会给女儿讲小石潭记了”“去年在西湖看到‘断桥残雪’,突然想起您说‘柳宗元写山水,是在写自己的孤傲’”。
“讲台是根,我也是”:她把南昌的烟火气,酿成了课堂的甜
刘欢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,赣江边的晨雾、绳金塔的庙会、老南昌拌粉里的辣酱,都成了她教学的“素材库”。讲端午的鸭蛋,她会带学生了解南昌“龙船节”的习俗;学故乡,她让学生采访家里的长辈,听他们讲“80年代的南昌是什么样”。
“教育不是把篮子装满,而是把灯点亮。”这是刘欢的座右铭。如今她带了徒弟,年轻老师问她“怎么才能让学生喜欢上课”,她总会指向窗外:“你先去爱这个城市,爱教室里这些鲜活的孩子。他们不是分数容器,是会发芽的种子。”
今年教师节,有毕业生从外地赶回来,给她带了一罐老家的蜜橘。“刘老师,您还记得吗?您说蜜橘要放放才甜,就像人要等等才懂道理。”剥开橘子,清甜的香气在办公室里弥漫,刘欢笑了,眼角有了细密的纹路——那是28年讲台岁月刻下的勋章,也是她最珍视的“成绩单”。
有人说,刘欢是南昌教育的一块“活化石”,但她自己却说:“我只是一棵站在讲台边的树,看着孩子们往更远的地方飞。”或许,真正的“好老师”,从来不是塑造完美的作品,而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课堂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光——就像刘欢常对学生说的:“愿你走出半生,记得当年教室里的阳光,记得那个和你一起读诗的清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