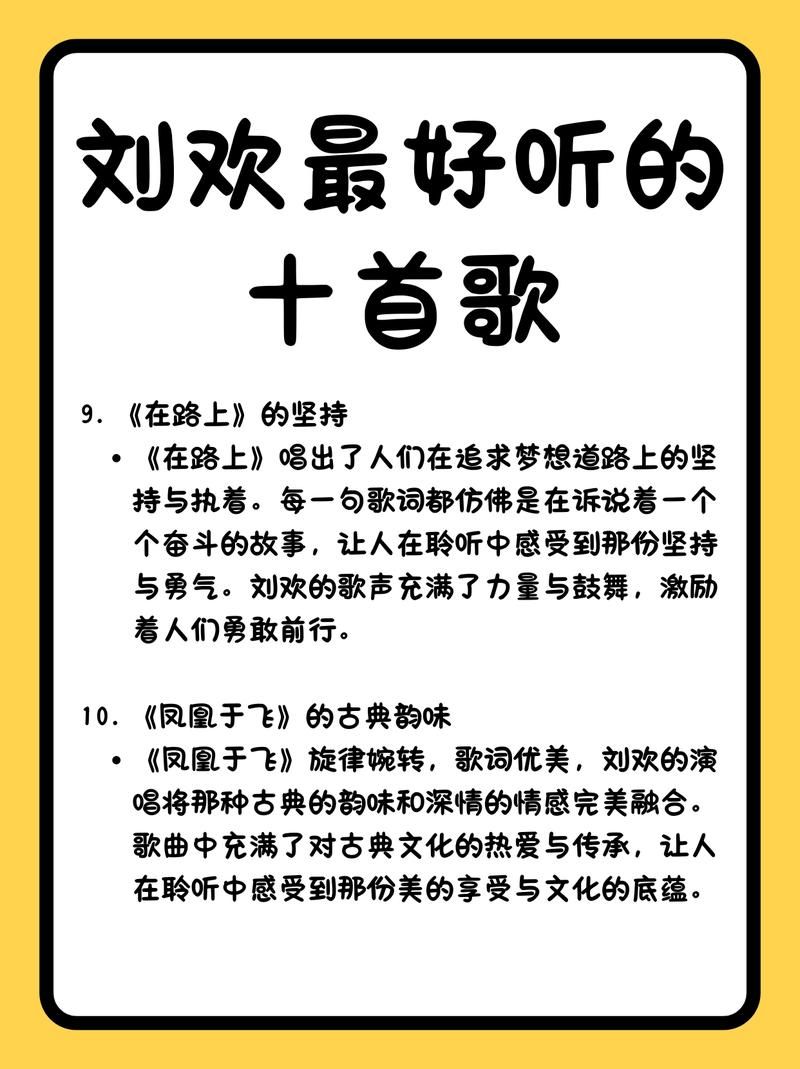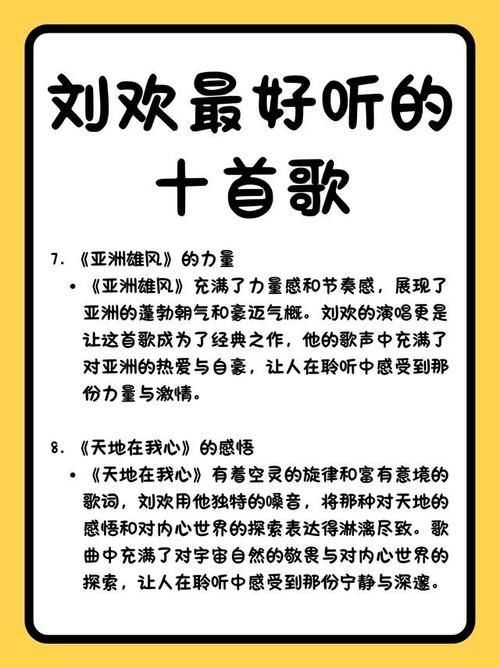清晨六点,赣南的薄雾还恋在山坳里,兴国县永丰乡的老樟树下,78岁的陈桂英拿着收音机,调到熟悉的频率——“刘欢的好汉歌,这人嗓子,跟咱们这里的山一样有劲儿。”她浑浊的眼珠里泛着光,像盛着一汪山泉。她或许不曾想到,这位在电视里唱了几十年的歌者,有一天会真的踩着泥巴路,走进这个地图上难寻的小村庄,和村民一起蹲在田埂上剥毛豆,听孩子们用方言唱山歌。

一、永丰乡的“红”与“静”:藏在深山里的文化根脉
永丰乡,藏在兴国县的褶皱里。这里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,当年“苏区干部好作风”的标语还斑驳地贴在老祠堂的墙上,村里八成老人都能讲出一段“送郎当红军”的往事。可“红”是它的底色,“静”却是它的常态——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,留守的娃娃们放学后唯一的娱乐,是在晒谷场跟着收音机学歌,学的大多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赣南民歌:采茶谣打支山歌过横排,调子婉转,带着泥土的腥甜。

“咱这儿的歌,是祖祖辈辈用命传下来的。”乡文化站站长李建国说,2018年乡里想办个“红色民歌节”,结果请来的老师听不懂方言,改编的歌失去了那股“山味儿”,孩子们唱得没精打采。就在他们犯愁时,北京来了位“老朋友”——刘欢。
二、“我这不是‘扶贫’,是‘寻根’”:他为何走进这片土地?
刘欢第一次来永丰乡,是在2019年的春天。不是作秀,不是演出,是跟着自己的公益基金“刘欢乡村音乐教育计划”做调研。他原以为来的是“需要被帮助”的地方,可老樟树下的一曲山歌,让他愣住了。
那天下午,他走进村口的老祠堂,几位老太太正围坐在一起,用本地方言唱十送红军:“一送红军下了山,秋风细雨缠绵绵……”没有伴奏,调子跑了几次,可那些哽咽的尾音,那些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拍着膝盖的节奏,让他眼眶发热。“这才是真正的‘原生态’!”他对同行的人说,“比录音棚里打磨出来的歌,有魂多了。”
后来他才知道,永丰乡的老人里,藏着不少“民间歌王”。72岁的邱石生曾是村里的赤脚医生,年轻时跟着老艺人学了上百首山歌,谁家办红白喜事,他都唱上一整天;65岁的刘冬秀,编竹篾的手艺一流,可唱起送郎歌,手指一动,眼泪就下来了。
“我一直觉得,音乐是‘阳春白雪’,可在这儿,它是脚上的泥、手里的汗,是老百姓日子的一部分。”刘欢在后来的访谈里说,“我不是来‘拯救’他们的,我是来‘寻根’的——寻咱们中国人最本真的音乐基因。”
三、从“教唱歌”到“育歌魂”:他给乡村留下什么?
刘欢没给永丰乡捐大剧院,也没给孩子们买昂贵的乐器。他做的,是“把根留住”。
他请来了音乐学院的教授,不是教孩子们唱流行歌,而是跟着村里的老人学方言民歌。祠堂里的课桌擦得发亮,黑板上写着“赣南古歌特点分析”,邱石生老人坐在讲台前,一句一句教孩子们“喊山”的技巧:“唱打支山歌过横排,得把‘横排’的‘横’字拉长,像我们这儿的山路一样,绕着绕着就上去了。”
更让他没想到的是,孩子们学得比他还快。10岁的李雨桐,父母都在广东打工,跟着奶奶长大,以前连话都说不利索,现在竟能把采茶谣改编成rap:“茶园青青茶香飘/阿妹背着茶篓走/哥你莫愁米和油/春天来了就有盼头。”
刘欢看到后笑了:“这才是真正的创作——把传统和当下捏在一起,比生搬硬套洋气多了。”
他还帮着村里整理民歌集。那些散落在老人记忆里的调子,被一一记下来:有的写在破旧的烟盒上,有的刻在竹筷子上,有的只是哼几句,录音师就得赶紧按住按钮。“这些歌,比任何文物都金贵。”刘欢捧着厚厚的永丰乡红色民歌集,像是捧着祖先的骨血,“咱们不能让它们跟着老人一起老去。”
四、双向奔赴:他从土地里汲取,他给土地以光
这几年,刘欢又来了三次。去年夏天,他带着永丰乡的孩子们登上经典咏流传的舞台,他们用方言唱的苔,让亿万观众湿了眼眶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
台下的陈桂英老人,红着眼眶给邻座的人解释:“‘苔花’就是我们山里的青苔,以前我们觉得它不起眼,现在才知道,它也开花。”
而刘欢,也从这片土地里,带走了更珍贵的东西。“我以前总说音乐要‘创新’,现在明白了,创新不是‘忘本’,是把老祖宗的东西用现代的方式讲出来。”他在一次音乐沙龙上说,“永丰乡让我重新理解了‘根’——没有根的花,开不长久。”
如今,永丰乡的“红色民歌班”已经成了村里的“文化名片”,连广东的游客都专程来听孩子们唱山歌。村口的民宿挂上了“刘欢音乐书屋”的牌子,书架上摆着他带来的音乐书,也有村民们自己写的歌本。
尾声:有些歌,是唱给天地听的
再回永丰乡,刘欢还是喜欢蹲在田埂上,听老人唱山歌。风吹过稻田,掀起一层层绿浪,孩子们的歌声混着虫鸣,飘得很远。
“刘欢老师,您说咱们的山歌,以后会一直传下去吗?”李雨桐仰着头问。
他摸摸她的头,指着远处的山:“你看那山,几千万年了还在,山歌也一样——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唱,就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或许,这就是最好的答案:当城市的音乐厅里回荡着华丽的旋律时,赣南的深山里,也有一群人,用最质朴的歌,守护着文化的根。而刘欢,就是那个牵线的人——他不只是“歌者”,更是一个“传歌人”,把土地的歌,唱给更多人听;把远方的光,还给土地本身。
有些歌,是唱给舞台的;有些歌,是唱给天地和历史的。刘欢与永丰乡的故事,或许就是后者最好的注脚——毕竟,真正的双向奔赴,从不是单向的给予,而是彼此的滋养与成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