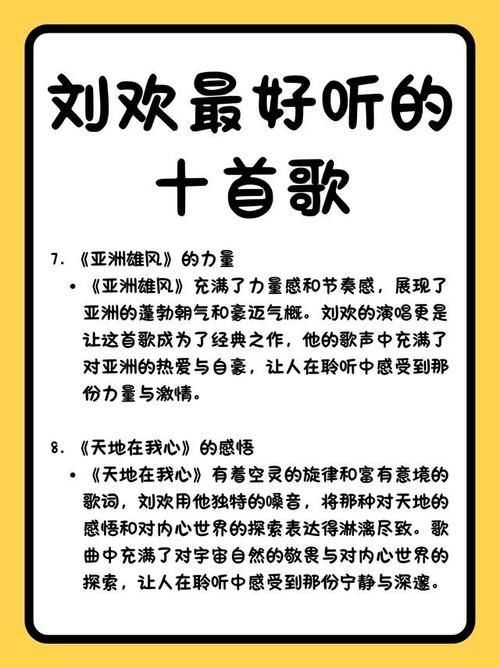清晨五点半,天刚蒙蒙亮,黑龙江绥化的兰西县还被裹在厚厚的白雾里。靠山村的村委会院子里,已经传来“咚咚锵锵”的锣鼓声——60岁的王淑兰正踩着节奏扭腰,手里的红绸子甩得呼啦啦响;旁边几个老爷们儿举着自制的“乐器”,搪瓷脸盆、不锈钢勺子敲得震天响;人群最前面,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人举着个旧扩音器,嗓子有点哑却依旧清亮:“婶儿!那个后转身腰再扭点儿!咱明儿可是要去邻村演的,可不能丢了脸!”
她叫刘欢欢,今年42岁,是靠山村公认的“文艺骨干”,也是十里八乡偷偷传颂的“民间团长”。
从“打工妹”到“返乡人”:她心里揣着个“文化梦”

刘欢欢的“文艺梦”打小就扎在根里。上世纪90年代的兰西县,冬天冷得呵气成霜,村里最热闹的地儿就是村头的大瓦房——每到傍晚,赶牛归来的村民、写完作业的孩子会围坐成一圈,听老人们唱二人转、唠西家长李家短。“那时候没电视,手机更是天方夜谭,”刘欢欢坐在村委会的木凳上,手里摸着已经磨掉漆的扩音器,嘴角扬起一丝回忆的笑,“我就蹲在窗根底下,听一句记一句,回家拿笤帚疙瘩当麦克风,对着土墙唱‘正月探妹正月正’,我妈总骂我‘疯丫头,没个姑娘样’。”
18岁那年,刘欢欢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背上行囊南下打工。在深圳的电子厂里,她每天加班12个小时,唯一盼头就是厂区广播放歌——听到熟悉的二人调配乐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。“工友们都爱听我唱大姑娘美,说那股子‘东北味儿’比原唱还冲。”刘欢欢笑着说,“可每到过年回家,看着村里老的老、小的小,年轻人走得只剩一半,心里就空落落的。”
2016年,父亲突发脑溢血,刘欢欢火速返乡照顾。忙完家里的事,她在村里转悠,却发现景象更冷清了:村西头的李婶守着个收音机打瞌睡,村东头的小年轻凑在一起刷短视频却没话聊,连小时候那个热闹的“说书场”也杂草丛生了。“那时候就觉得,日子不能这么过啊!”刘欢攥紧了手里的扩音器,“粮食丰收了,腰包鼓了,可心咋就空了呢?”
她把“舞台”搬到田间地头:谁说农民不能有“文艺范儿”?
刘欢欢下了决心:要给村里建个“文艺队”。可这话一说出来,就有人戳她脊梁骨:“一个农村妇女,自己家日子还顾不过来呢,整啥文艺队?能当饭吃?”就连丈夫也劝她:“别瞎折腾了,好好种地、照顾孩子比啥不强。”
刘欢欢没听劝,她有自己的“小算盘”:“咱农民种地是本分,但日子也得有乐子啊!再说,年轻人为啥往外跑?不就是觉得村里‘没意思’?咱要是把文化搞起来,说不定他们就愿意回来了!”
她先从“挖人才”开始:村里的老教师王建国,会拉二胡,退休后没事就自己在院里瞎拉,刘欢欢提着两瓶酒登门:“王叔,您拉那骏马奔驰保边疆,比电台里播放的还带劲!咱村要是能有个文艺队,您当‘艺术总监’,咋样?”王建国一开始直摆手:“我这都老胳膊老腿了,哪还整得了这些。”刘欢欢硬是把二胡塞进他怀里:“您就带带大伙儿,我组织人,咱不求多专业,图个乐和!”
接着,她挨家挨户请“演员”:60多岁的王淑兰,老伴去世早,一个人带孙子,刘欢欢去帮她挑水、剁菜,趁着孙子不在跟前,小声说:“婶儿,您还记得不?小时候您扭大秧歌,那叫一个好看!咱现在组个队,您当‘领舞’,孙子回来看到,肯定骄傲!”王淑兰抹了把眼泪:“现在老了,扭不动了。”“咋扭不动?我陪您练!咱慢慢来!”
最难的是道具和服装。刘欢欢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的存款取了出来,跑到县城的批发市场,挑了最便宜的红绸子、黄马甲,又花200块钱买了台二手音响。“当时我儿子气得直跺脚,说‘妈你疯了,那是我的婚房钱!’”刘欢欢嘿嘿一笑,“我告诉他,妈给你‘攒’了个更大的‘家’——等咱文艺队火了,全村的人都乐呵呵,比你结婚还重要!”
零下20度的排练场:冻僵的手指里,攥着“对好日子的盼头”
2017年冬天,靠山村“文艺队”正式成立了。可谁也没想到,第一场“排练”就遇上了大难题。
村里没有活动室,只能在村委会的院子里。东北的冬天,零下二十多度是常态,风刮在脸上像刀割。刘欢欢带着大伙儿生了个铁皮炉子,可风一吹,火苗直往旁边窜,炉盖刚盖上去,就被吹开了。“冻得实在受不了,我们就跑着取暖,跳几支舞,再围着炉子搓搓手。”王淑兰说着,伸出布满老茧的手,“那时候手上的冻疮没好过,裂口子一碰就出血,可没人说‘不干了’。”
当时刘欢欢的儿子正上高三,每天晚上写作业到10点,她就陪着排练到10点。“儿子总说‘妈,你能不能管管我?光管别人家孩子’。”刘欢欢眼里闪过一丝愧疚,“但有一次,他写完作业,悄悄站在院门口看我们排练,后来跟我说‘妈,你们扭得真好看,比电视剧还有意思’。”
排练的节目也都是“接地气”的:唱的不是青藏高原这种“高音曲”,而是改编的咱们村里有力量,词儿是刘欢欢现编的——“玉米金灿灿,水稻摇铃铛,总书记的关怀暖洋洋,咱们农民的日子,一年更比一年强”;演的不是才子佳人,而是村里真实的故事——李二婶的菜园子,讲的是李二婶一个人种了5亩菜,缺人手时全村来帮忙,最后菜卖了个好价钱,请大家吃席的故事。“演李二婶的是我的邻居张婶,她本身就爱唠叨,演起来比专业演员还像,”刘欢欢笑着说,“演帮忙村民的,都是真的来帮过李二婶种地的,台上台下,情绪都一样。”
慢慢的,文艺队的人从最初的10多个人,变成了50多个人,连村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开始打电话问:“欢欢姐,咱文艺队还招人不?我过年回来,也想扭两下!”
从“村里演”到“全网火”:那个田埂上的“文化火种”,烧得更旺了
2019年,兰西县要举办“乡村文化节”,刘欢欢带着文艺队报了名。站在县里的舞台上,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,王淑兰紧张得直哆嗦。“欢欢,咱要是演砸了,可咋整啊?”“婶儿,怕啥!咱演的是咱自己的日子,错不了!”
他们演的李二婶的菜园子,一上台就炸了场。熟悉的方言、真实的故事,让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,不少人还偷偷抹眼泪。这个“土掉渣”的节目拿了全县一等奖。
“那天从县里回来,村口站满了人,放鞭的、拍巴掌的,比过年还热闹。”刘欢欢说,“王建国叔叔抱着二胡,边走边拉,泪珠子掉在琴弦上,啪嗒啪嗒响。”
这之后,靠山村文艺队出了名。周边的村都来请他们演出,县里、市里的文化活动也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刘欢欢还琢磨着“与时俱进”:买了手机支架,让在外打工的队员用视频连线排练;跟着年轻人学剪短视频,把演出的片段发到网上,没想到几十万播放量。“有个在外打工的小伙子给我留言:‘欢欢姐,看了你的视频,我想家了。今年我回来,一定加入文艺队!’”
更让刘欢欢高兴的是,不少年轻人真的回来了。大学毕业的小张,放弃了城里白领的工作,回村开了个“农家乐”,专门给文艺队当“排练基地”;在外打工的小李,回来买了台二手摄像机,成了文艺队的“专属摄像师”。“他们都说,‘原来咱农村也能这么有奔头’。”刘欢欢的眼睛亮晶晶的,“我现在觉得,当年我那点‘文化梦’,真的在慢慢实现。”
结尾:那些藏在泥土里的“光”,才是真正的“顶流”
现在的刘欢欢,每天还是忙得脚不沾地。除了组织排练,她还在村里办了个“文艺小课堂”,教小孩子唱二人转、扭秧歌。“前几天有个4岁的小丫头,上台唱小拜年,奶声奶气的,把所有人都唱乐了。”刘欢欢笑着说,“你看,文化这东西,不管多大岁数,不管在哪儿,都能生根发芽。”
其实,在兰西县像刘欢欢这样的“民间团长”,还有很多。她们可能没有华丽的舞台,没有聚光灯,没有粉丝,却用自己的热情和坚持,把文化的种子撒进了乡村的泥土里。她们让留守的老人不再孤独,让返乡的年轻人找到归属,让“乡村文化”不再是书本上的词儿,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烟火气。
或许我们习惯了追逐舞台上的“顶流”,习惯了为明星的闪耀欢呼,但真正让生活有温度、让日子有盼头的,往往是这些在田间地头、在寻常巷陌默默发光的普通人。她们就像兰西县冬天里的那团火,虽然微弱,却足够暖人心窝——毕竟,能让乡亲们扭着秧歌、笑着唱出“好日子”的人,本身就是最厉害的“造梦师”啊,不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