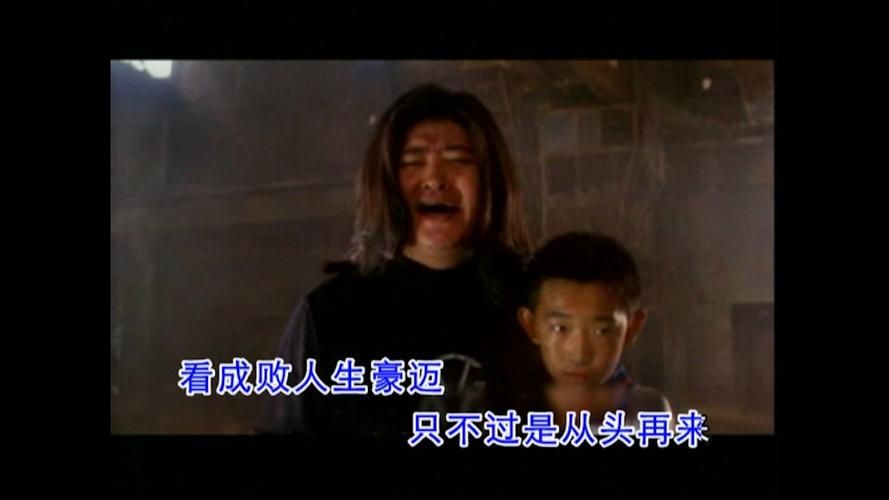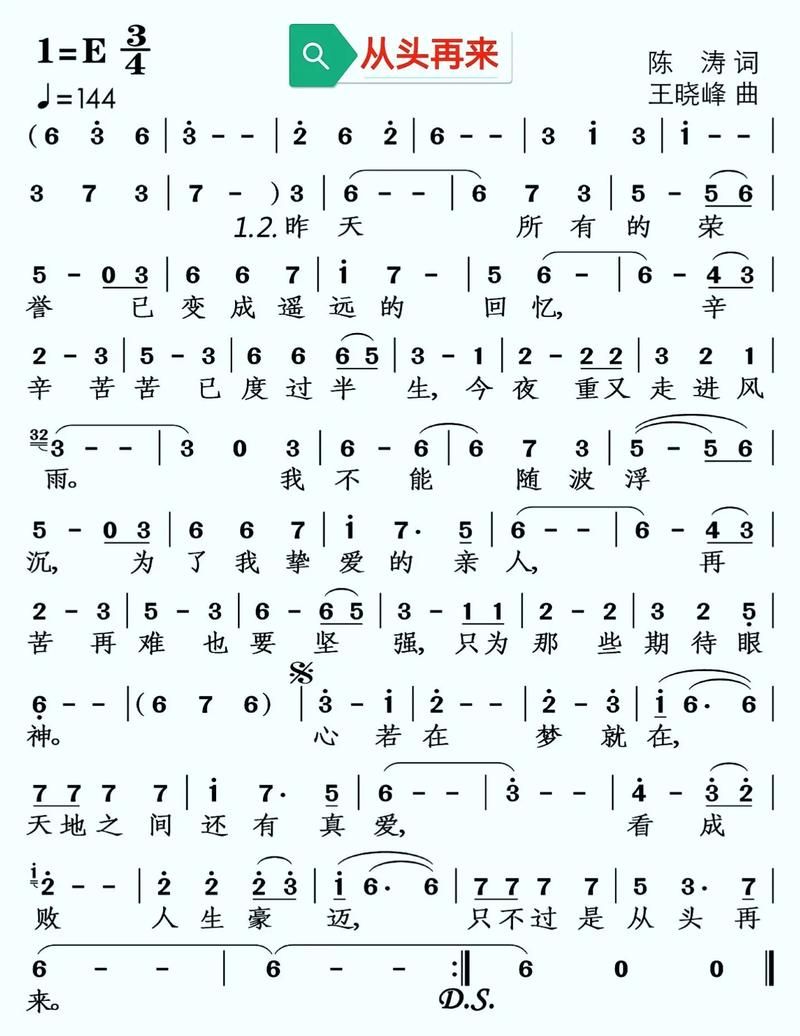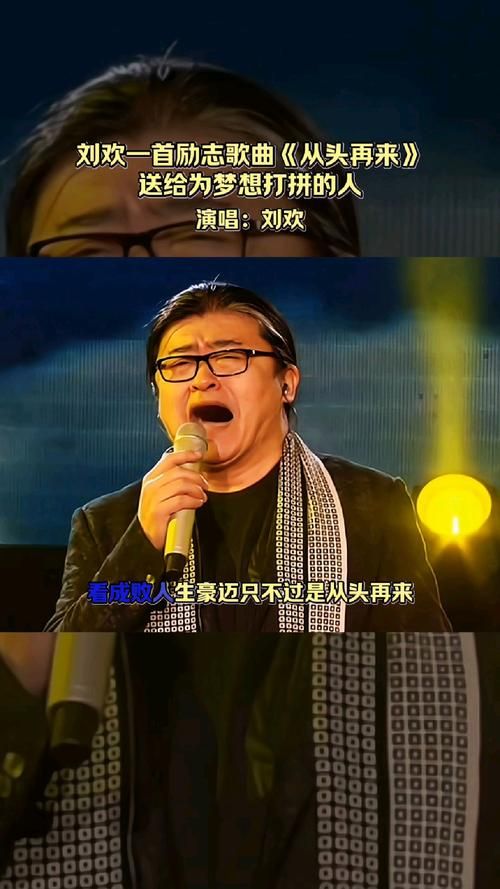午后的阳光斜切进仁化周田中学的教室,落在讲台上那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身上。他手里捏着半截粉笔,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“八卦图”,突然回头问:“同学们,你们觉得诸葛亮借东风,是运气还是懂气象?”底下瞬间炸开锅,有的拍着桌子喊“肯定是装神弄鬼”,有的皱着眉翻课本,直到他指着图上的“巽卦”笑着说:“看这儿,易经里早说东南风多,诸葛亮在江边待那么久,能不看不懂?”
教室里先是一片静默,随即爆发出掌声——这场景,在刘欢的语文课上,几乎是每天都会上演的“固定节目”。
从“催眠课本”到“行走的活教材”:他把知识“喂”进了学生心里

在周田中学,很多学生刚上刘欢的课时,都会偷偷嘀咕:“语文课不就是读课文、背古文?能有啥意思?”可第一次课下来,他们就发现:“刘老师的课,像追连续剧,根本走神不了。”
教赤壁赋时,他不讲“诵明月之诗”的翻译,而是先放段长江边的浪涛声问:“假如你是苏轼,被贬到黄州,突然听到这个声,会想啥?”有学生说“孤独”,他说“对,但你看他接着写‘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’,这孤独里藏着啥?”;讲到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,他拿出手机翻出老家周田镇的老照片:“你们看,二十年前我们学校教室漏雨,现在不漏了,可杜甫一千年前就盼着‘大庇天下寒士’,这算不算‘穿越时空的梦想’?”
他的办公室抽屉里,永远塞着“稀奇古怪”的东西:讲水浒传时掏出把朴刀模型(虽然是塑料的,但学生们抢着摸),讲诗经时带学生在校园里找“荇菜”,甚至连讲病句,都能编成顺口溜:“‘的得地’分不清?记住‘白的(形容词)吃不得(动词),得(动词)到一张白(形容词)纸,地(名词)上画只得(动词)意的小狐狸’——记住了没?”
“以前背出师表总背串,刘老师让我们把诸葛亮当‘客服’,给刘备写‘工作报告’,‘先帝创业未半,而中道崩殂’就是‘老板(先帝)的项目刚起步,人突然没了’,一下子就记住了!”初三学生李晓萌说,现在她最期待的就是语文课,连做梦都在琢磨“刘老师下节课会掏啥‘宝’”。
不是“网红”,却成了学生们口中的“欢哥”:他用真心换真心
在周田中学,没人叫他“刘老师”,一律“欢哥”——这称呼不是因为他年轻,而是因为他“蹲得下身子”和学生们“玩”在一起。
去年冬天,学生小林因为父母吵架,连续一周没上课,缩在宿舍里哭。刘欢没去“说教”,而是提了袋橘子坐在他床边:“我上高中时,也跟我爸吵过架,说三天没理他。结果第四天他给我送饭,装了双我爱吃的鸡腿,上面还留了个牙印。”他剥开橘子,递过去:“你爸妈估计也牙疼呢,要不要回去给他们递个橘子?”后来小林回了家,父母专门到学校道谢,刘欢摆摆手:“别谢我,橘子是小林自己挑的。”
对“调皮蛋”,他有独一套“招数”。学生小周上课总睡觉,刘欢没当众骂他,而是每天早上给他带个热包子:“我知道你家远,起得早,没吃早饭吧?以后上课困了,就悄悄掐自己大腿,别睡,我给你留着包子,下课吃。”三个月后,小周的作文热包子里的温度在县里拿了奖,里面写:“刘老师的包子,比我妈煮的还香,因为里面藏着我没说出口的‘谢谢’。”
“欢哥从不觉得我们‘笨’,”毕业多年的陈浩说,他当年成绩垫底,刘欢每天放学留他半小时,“不是补课,是聊天‘聊成绩’——‘你喜欢打篮球?那投篮命中率怎么算?就是总分除以总投篮次数啊,你这次语文60,上次50,命中率提高20%,这就跟投篮手感回来了一样!”后来陈浩考上了体育学院,现在当了教练,总跟学生说:“学习跟打球一样,有人教你怎么‘发力’,比你自己瞎琢磨强一百倍。”
三尺讲台外的“顶流”:他让教育有了“烟火气”
很多人觉得“名师”就该端着,可刘欢偏要“接地气”。他的手机相册里,存的不是获奖证书,而是学生画的小漫画:上面有个戴眼镜的“光头老师”,举着粉笔画歪嘴,旁边写着“欢哥上课,笑出八颗牙”;他的朋友圈,很少发教育心得,多是“今天学生给我摘的枇杷,甜过蜜”“帮小周改的作文,他居然用了‘春风十里不如你’,这小子,懂浪漫啊”。
去年县里搞“优秀教师评选”,有人问他:“你最大的成绩是啥?”他指着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照片——那是去年教师节,学生们偷偷给他拍的:他趴在桌子上睡着,学生们围着他,桌子上摆满了鲜花和写着“欢哥辛苦了”的纸条。“你看他们拍我时,眼睛里的光,比啥奖都亮。”
如今,刘欢已经教了18年,带过10届毕业班,他带的班,语文平均分连续8年全县前三,可他觉得“这不算啥”,最得意的是“每年都有学生给我写信,说‘老师,我现在也当老师了,因为你’”。
仁化周田中学的老校长说:“刘欢啊,就是把教育‘揉碎了’喂给学生。”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,没有刻板的说教,他用一张旧地图、半截粉笔、一袋热包子,把知识的种子种进学生心里,再用真心浇灌,让它长成了“会发光的样子”。
或许,真正的“名师”,从来不是光环下的“顶流”,而是像刘欢这样——站在三尺讲台,守着一方天地,用一辈子的时间,回答“怎么才算好老师”这个问题的普通人。而那些被他点亮的学生,会带着他的光,走向更远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