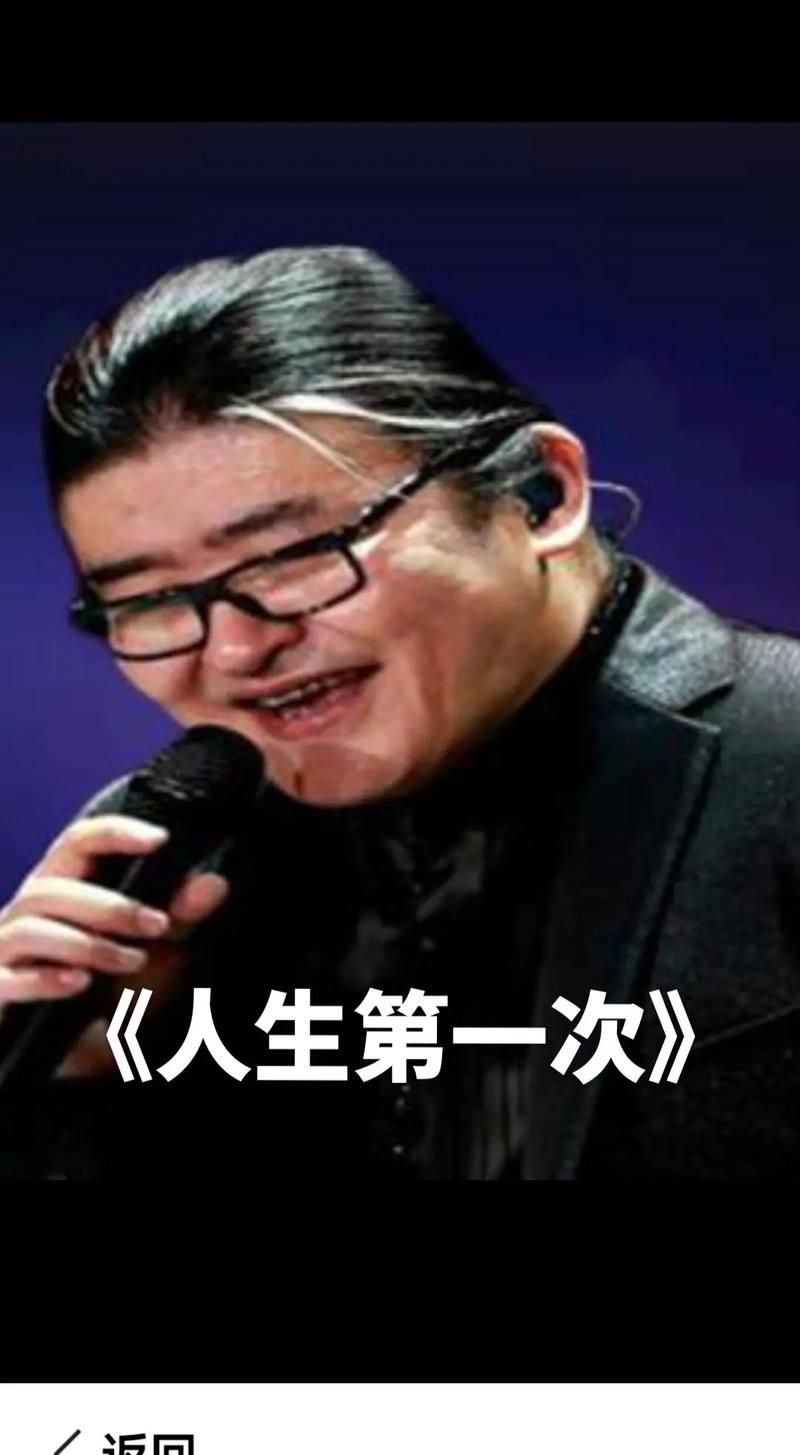如果只用"歌手"定义刘欢,那大约就像用"演员"定义周星驰——总觉得哪儿不对,却又说不上来。大多数人熟悉他穿着皮夹克、声如洪钟地唱"路见不平一声吼",却少有人注意到,这位"乐坛常青树"的简历里,还夹着一把磨得发亮的老二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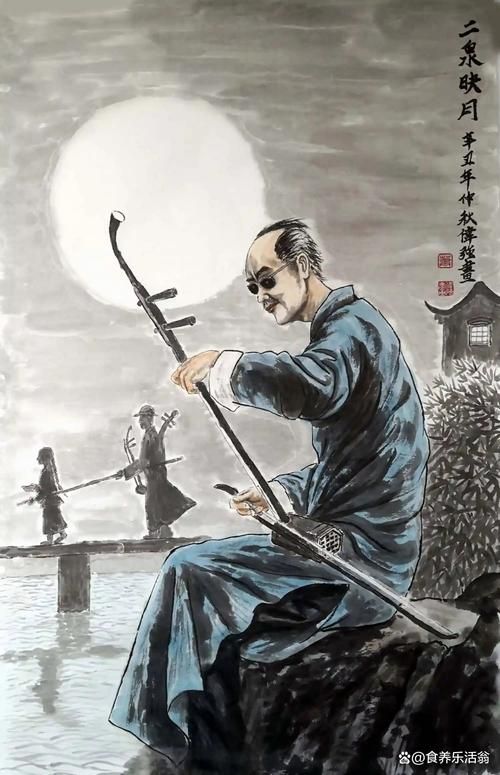
从琴房到舞台:二胡是他最早的音乐"启蒙老师"
1959年出生在天津的刘欢,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不是收音机里的流行歌,而是父亲那把旧二胡。父亲是普通工人,却酷爱民乐,没事总爱拉几句二泉映月。七八岁的刘欢缠着学,父亲不教——"拉二胡得有苦功夫,你这种调皮鬼坐不住。"他偏不信邪,趁父亲上班偷拿出来,用小小的手指按得琴弦发红,吱吱呀呀拉出来的调跑得比天津快板还远。

邻居李阿姨是小学音乐老师,实在听不下去,敲开他家的门:"这孩子手指头挺长,我教他吧。"就这么着,刘欢的琴房生涯开始了。每天放学后别的小朋友满街跑,他抱着二胡坐在窗边练,赛马里的快弓拉到手臂酸, 江河水里的滑音拉得眼泪汪汪,最怕的是练战马奔腾,老师说"得听见马蹄声在琴弦上蹦",他练到琴筒上的蟒皮都磨得发亮。
后来考上北京国际关系大学,学的和音乐八竿子打不着,但宿舍里总少不了二胡声。同学聚会别人唱歌,他抱着二胡即兴伴奏,把外婆的澎湖湾改成二胡版,把我的祖国的副歌用快弓拉出气势,全系都知道:"那个国关系的小子,二胡比唱歌还溜。"

歌坛顶流为何从不丢下二胡?
1987年,刘欢凭少年壮志不言愁一炮而红,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歌手。演唱会一场接一场,通告排得比春运火车票还满,可在酒店化妆间,他总带着一个黑色的琴盒。有一次后台准备,工作人员问:"刘老师,今天不用二胡吧?"他一边往手指上缠松香一边笑:"谁知道呢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想拉一段。"
真正让观众意识到"刘欢和二胡的不解之缘",是1990年的北京春晚。他唱了Theme from Schindler's List(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),唱到一半突然停下来,乐队里二胡声缓缓响起,那把熟悉的音色替代了西洋弦乐,把哀婉又磅礴的情绪推到顶峰。后来采访,他说:"当时导演没设计,我看着歌词里的'夜太漫长,无处暗生长',突然觉得二胡更适合表达这种藏在骨子里的苍凉。"
更绝的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,他在鸟巢唱我和你,正当全世界沉浸在钢琴与童声的纯净中,舞台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二胡——那是他提前和音乐总监沟通的"彩蛋",用茉莉花的旋律做铺垫,让这首歌既有东方韵味,又不失国际视野。"二胡不是'老古董',它是会说话的乐器,"后来他做节目时说,"我想让年轻人知道,这玩意儿比他们想的酷多了。"
二胡独奏家的"隐藏简历",比歌声更少人知
如果说歌手刘欢是大众眼中的"顶流",那么二胡独奏家刘欢,更像是只存在于音乐圈"传说里的人"。圈内人常说:"刘欢拉二胡,是'歌手的严谨,加上民乐人的魂'。"
1995年,他在北京音乐厅办了场个人音乐会,前半场唱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,后半场抱起二胡拉起了二泉映月赛马。最后压轴的是他自创的弦歌行,把京剧的西皮导板、昆曲的水磨腔揉进二胡技法,高潮处快弓拉到头发丝都在颤,底下观众听得鸡皮疙瘩掉一地。一位民乐界的泰斗后台拍着他肩膀:"你这技术,够得上专业院团的独奏家水准。"
这些年,他很少自称"二胡演奏家",但做的却是推广民乐的事。给宋祖英的民乐音乐会做艺术指导,用二胡帮萨顶顶编曲,甚至在综艺节目里,一把二胡"怼脸"拉难忘今宵,把观众听得目瞪口呆——原来这把老伙计,能玩出这么多花样。
前两年有网友翻出他20年前在大学讲座的视频,他穿着白衬衫坐在讲台上,怀里抱着二胡给学生说:"你们年轻人觉得二胡土?我告诉你们,它可是唐朝就有 '胡琴',比小提琴年纪大多了。拉好二胡,得'懂人心',拉赛马你得看见草原,拉病中吟你得尝遍苦辣。"视频传到网上,评论区炸了:"求刘老师开二胡专场!""原来这才是顶流隐藏技能!"
结语:那个把二胡"拉活"的人,或许更懂音乐的魂
从天津老房子的琴房,到鸟巢的奥运主舞台,从好汉歌的豪迈到二泉映月的悲怆,刘欢手里的二胡,从来不是"才艺展示",而是他理解音乐的另一种语言。有人说他"浪费天赋"——明明能当歌王,却总抱着把老琴磨;但他自己知道:"二胡教会我的,比唱歌更多。它告诉我,音乐得有根,根扎在泥土里,才能长得高。"
下次再听到刘欢唱歌,不妨想想:那个声如洪钟的汉子,或许正对着窗外练琴呢。蟒皮震动的嗡鸣里,藏着一个歌手最柔软,也最骄傲的民乐江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