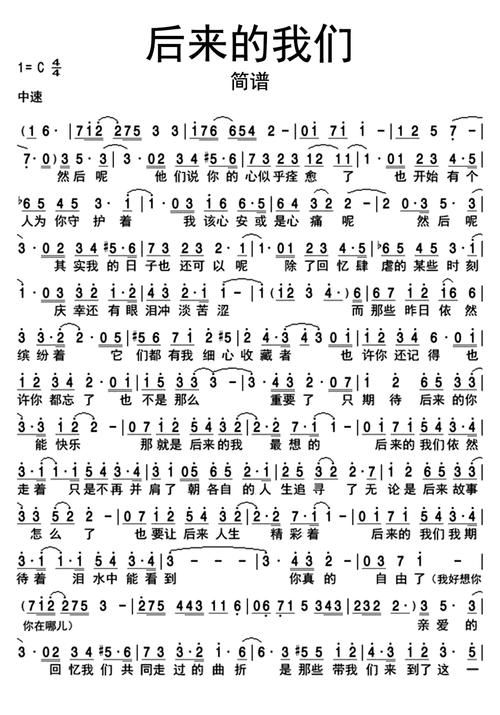下午五点的丹凤中学,铃声刚响,高三(7)班的门口就挤了几个学生,手里捏着练习册,七嘴八舌地喊:“刘老师,这道题我昨天想了半夜,您昨天说的‘等效替代法’,是不是能用在受力分析上?”
一个扎着马尾、穿着浅蓝色衬衣的女人从教室里探出头,眉眼弯弯,手里还捏着半截粉笔:“来来,我看看你们想的和我的法子是不是一条路。”
她是刘欢欢,丹凤中学的物理老师,学生们私下叫她“欢姐”,但更多人喊她“物理魔法师”——这外号不是白来的,在她手上,那些让中学生头疼的“F=ma”“楞次定律”,总能变成手里转的魔圈、窗外飘的气球,甚至食堂阿姨颠勺的抛物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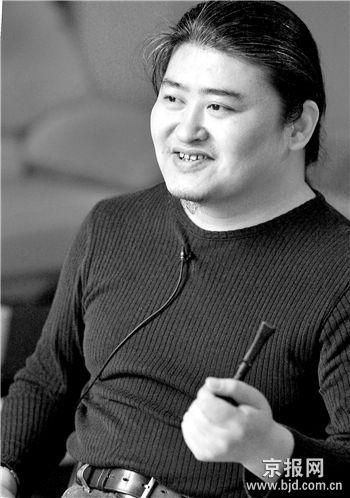
“物理不是背公式,是拆解生活里的‘魔术’”
第一次听刘欢欢讲课,以为是走进了科学小品的现场。讲“自由落体”,她没急着抛公式,而是从兜里摸出一张纸和一支粉笔,同时松手:“你们猜,谁先落地?”
学生异口同声:“粉笔!”她却不慌,把纸揉成一团,再丢:“现在呢?”教室里突然安静了——“一样?”“不对,纸团还是慢?”她笑着接住落下的粉笔:“物体下快慢,不看轻重,看空气阻力。要是把纸摊开,蒙在粉笔上一起丢……”话没说完,前排男生已经抢过纸片,跟着老师比划起来。
讲“圆周运动”,她带着学生去操场。男生打篮球,她掏出秒表:“你们拍球时,指尖和球的接触点,做的是圆周运动对吧?试试算算它的角速度。”女生跳皮筋,她蹲在旁边观察:“橡皮筋的形变,是不是跟弹力公式有关?”下课铃响时,学生才发现,一节物理课,连课本都没翻开过,却记住了十几个生活中的例子。
“欢姐的课,像拆盲盒。”课代表林晓宇说,“昨天讲‘电磁感应’,她抱了个旧收音机进来,拆开线圈,拿磁铁在里面蹭:‘听见没?这是电流的声音。’我们当时都愣了,原来物理不是课本里的黑体字,是能摸着、能听着的。”
“学物理,得先让学生敢‘错’,别怕当‘笨蛋’”
刘欢欢的办公桌抽屉里,有个蓝色的“错题本”收集盒,里面全是学生的卷子——有的画着哭脸,有的写着“我真蠢”,有的被撕掉又粘好,还贴着便利贴:“刘老师,这题我错了五次,但这次好像懂了。”
“我当老师十年,见过太多学生怕物理,”她翻开一沓卷子,指着一道画满红叉的力学题,“你看这道题,学生第一次做错了,我给个叉;他第二次还错,我又给个叉,第三次呢?要是还是叉,他直接就放弃了。”她的做法是:第一次错,画个笑脸,旁边写“这里藏着个小陷阱哦”;第二次错,打个问号,“看看你的受力图,是不是漏了摩擦力?”直到第三次,学生自己把题做对,她才在旁边画个星星:“你看,侦探不都靠错案找线索吗?”
去年有个男生叫小杰,物理考过19分,上课睡觉,作业从来不动。刘欢欢没骂他,而是把他叫到办公室,指着窗外的篮球架:“你投篮准不准?”小杰来了精神:“班里前三!”“那你知道投篮时,球的初角速度和出手高度怎么影响命中率吗?这是物理里的‘斜抛运动’啊。”她掏出纸笔,一边画图一边算,小杰的眼睛慢慢亮了。后来,小杰不仅物理及格了,还带着几个同学组了个“投篮物理研究小组”,期末考了全班第五。
“欢姐常说,错题是学生的‘勋章’,”同事王老师说,“她从不批评‘笨’,只会问‘你从这个错误里偷到了什么?’”
“老师不是‘标准答案’,是陪学生找‘为什么’的同行者”
在丹凤中学,刘欢欢是出了名的“课疯子”——为了讲“光的折射”,她顶着大太阳去操场看太阳光透过眼镜片的角度;为了讲“声波”,她自学口琴,在课堂上吹茉莉花,让学生摸着嗓子感受振动。有次讲“热力学第二定律”,学生问她:“老师,那宇宙最后是不是会热寂啊?”她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:“这个问题,连爱因斯坦都还在想呢。不如咱们一起查资料,下次课开个‘宇宙猜想大会’?”
她的教案本里,夹着学生的小纸条:“刘老师,为什么冰箱门打开时会发光?”“为什么冬天梳头发头发会炸毛?”“您说物理能解释爱情吗?我好像有点懂了‘万有引力’……”这些问题,她都认真回复,有的写满一页纸,有的画个爱心加个公式:“爱情不是F=mg,是F=kx?x?/(r+r?)2——你懂我的吸引力,我懂你的倔强劲儿。”
今年教师节,毕业多年的学生给她寄来一张照片:照片里的男生站在实验室里,白大褂上别着“物理竞赛一等奖”的徽章,背后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,上面是刘欢欢当年写的:“别怕路远,我们慢慢走。”
结语:讲台上的“明星”,没有聚光灯却有光
有人说,娱乐圈的明星靠流量和颜值,但丹凤中学的刘欢欢,靠的是粉笔灰里的耐心、公式旁的巧思,还有那句“物理不难,只要你愿意和我一起拆生活这个‘魔术盒’”。
傍晚六点,刘欢欢锁上办公室的门,教学楼里的灯次第亮起。她抬头看了看高三(7)班的窗户,那里还有几个学生围在一起讨论题目,笑声裹着晚风飘出来。她笑着挥挥手,转身走进暮色里——没有聚光灯,没有尖叫,但那些因为物理眼睛发亮的学生,就是她最亮的“星光”。
讲台很小,装得下三千物理法则;老师很普通,却让无数平凡的日子,长出了探索的翅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