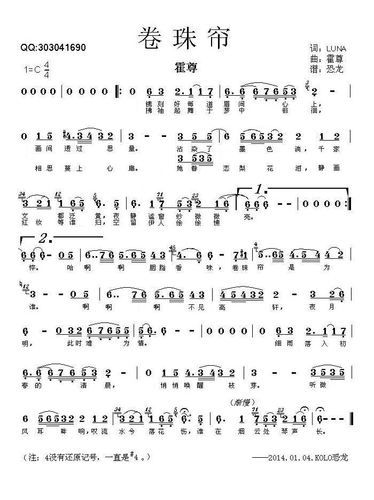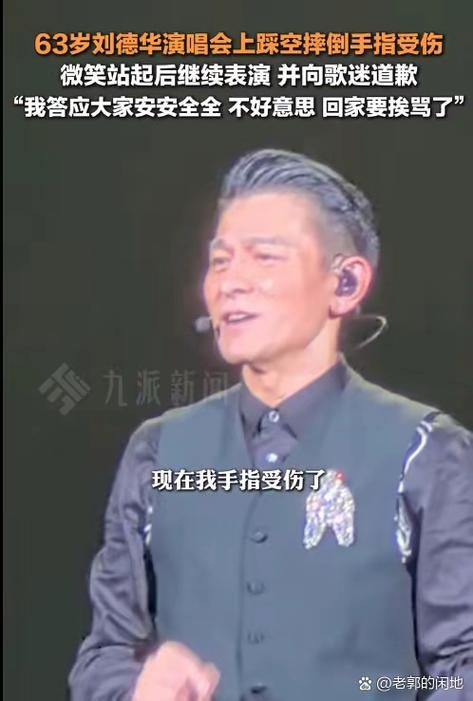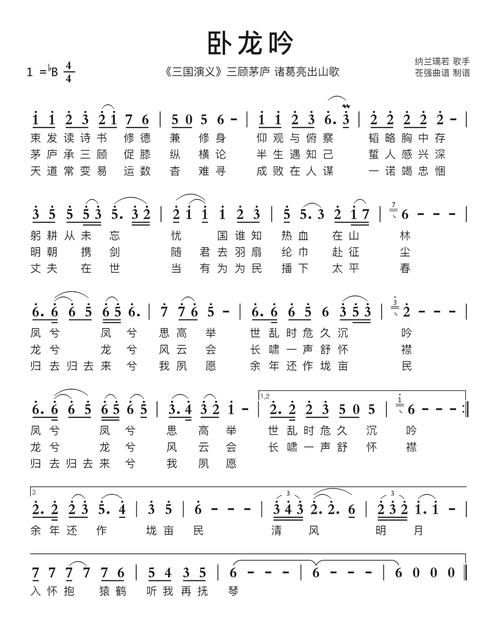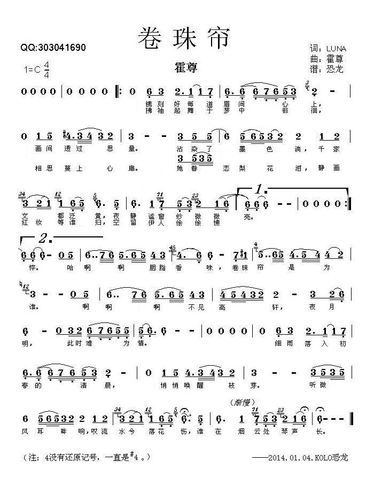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?在某个寻常的街角,被一阵不成调却格外用心的歌声拽住脚步——或许是一早挑着担子卖老友粉的大叔,边翻搅铁锅边哼着几句彩调;或许是傍晚聚在公园下棋的老人,赢了棋就扯开嗓子唱段邕剧。在南宁,这样的“民间歌者”从不稀罕,但“合唱团里走出来的刘欢”,却是个会让邻里笑着摇头的“特别存在”。
“别瞎猜,我就是个爱瞎哼的退休老教师”
第一次见到刘欢,是在江南区那个老旧的合唱团活动室。门没关严,一阵混着跑调的合唱声从里面漏出来,像掺了沙子的邕江水,却偏偏有种让人挪不动步的劲儿。推门进去,一个穿藏青夹克、头发花白的老伯正挥着胳膊指挥,左手食指跟着旋律画圈,右手比划到兴起,袖口的粉笔灰落在前排阿姨的白发上,两人都没顾上擦。

“您是……刘欢?”我看着合唱团墙上那张“社区合唱大赛二等奖”的合影,中间站着的指挥老人,和记忆里央视屏幕上那个唱弯弯的月亮的歌手重影,又完全不像。
老人摆摆手,露出被烟熏黄的牙:“嗨,重名!我叫刘欢,南宁土生土长的‘欢叔’,58年生的,退休前是教语文的。什么‘歌王’,就是退休闲得慌,带街坊们唱唱歌。”他转身从抽屉里翻出个搪瓷缸,倒了杯茉莉花茶,茶渍把缸子染成了焦糖色,“喏,天冷了,喝口茶暖和。你要听歌?我让她们再唱一遍山歌好比春江水,不过啊……得用我们南宁白话试试。”
“五音不全?在我这儿,敢张嘴就是好嗓子”
合唱团里,有刚退休的银行职员,有摆菜摊的王婶,有带孙子的李奶奶,最大的是78岁的张大爷——一开始,张大爷连简谱都不认识,每次排练总躲在角落,说自己“五音不全,别丢人”。
“张伯,您会唱浏阳河不?”刘欢突然指着他,张大爷脸涨得通红:“欢叔,我真的……不会……”“谁说不会?您昨天带孙子,不就哼了‘浏阳河,过了九道弯’吗?调子都对!”刘欢掏出手机,点开一段录音,张大爷的声音混着孙子的笑声,调子跑得像坐过山车,却在刘欢的笑里变得格外有底气。
后来,张大爷不仅敢开口,还主动要求唱男低音。王婶更绝——白天在菜摊用吆喝调练嗓子,傍晚就把刚摘的空心菜往刘欢怀里塞:“欢叔,你尝尝,吃了我菜,下次排练得给我多教两句高音!”
“她们啊,图个乐子。”刘欢揉了揉被拍肩的王婶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,“上次社区搞活动,李奶奶非要唱万水千山总是情,唱到‘山也绵绵水也长’,忘词了,急得直拍大腿。我赶紧带着大家一起‘嗯嗯啊啊’接上,观众还给我们鼓掌呢——你看,唱歌哪有什么标准?开心就好。”
“用邕剧腔唱红歌,是我们南宁人的浪漫”
去年国庆,合唱团要参加社区演出,选了我和我的祖国。排练时,大家总觉得“旋律太温柔,不够有劲儿”。刘欢挠了半天头,突然一拍大腿:“咱们加段邕剧牌子!老南宁人都懂那个味儿!”
于是,原本舒缓的旋律里,硬生生插进了“依呀嘞”“哟喂”的拖腔,王婶的邕剧小嗓和李爷爷的粤腔混在一起,像老友粉里的酸笋和豆豉——初听有点冲,细品却满是烟火气。演出那天,刘欢指挥到兴头上,干脆把夹克一甩,用浓重的南宁白话喊:“邕江的水也甜咧,咱们唱得再响一点!”台下观众愣了三秒,接着哄堂大笑,有人跟着节奏拍腿,还有人吹起了口哨。
“后来有年轻孩子跑过来说,原来红歌也能这么唱!”刘欢眼神亮亮的,像藏着邕江的波光,“南宁嘛,就是个包容的城市——老友粉要酸辣,彩调要诙谐,唱歌也得有点自己的土味道。我教他们,别学电视里那些‘标准唱法’,你们是南宁人,得把邕江的风、老巷子的雨,都揉进歌里去。”
“欢叔的合唱团,是我们老街坊的‘第二个家’”
活动室墙上,挂着张特别的照片:刘欢穿着红马甲,站在一群老人中间,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束茉莉花。照片旁边的便签纸上是王婶的字:“欢叔说,茉莉是南宁的市花,歌也要像茉莉香,慢慢飘。”
“去年我老伴走了,那段时间天天在家掉眼泪,是欢叔硬把我拉来的。”李奶奶捏着谱子,手指关节有点变形,“刚开始唱不出来,一开口就哭,欢叔也不劝,就给我倒杯茶,说‘慢慢来,歌是唱给自己的’。现在啊,我每天不唱两句,晚上觉都睡不好。”
刘欢坐在角落的旧藤椅上,闭着眼睛听大家唱歌,阳光从窗户漏进来,落在他洗得发白的夹克上,像撒了一层金粉。我突然明白,为什么南宁人说他和“央视刘欢”不一样——他从不飙高音,却把每个音符唱进了街坊们的心里;他没拿过什么大奖,却把合唱团变成了老街坊的“第二个家”,让那些被岁月压弯了腰的脊梁,在歌声里重新挺直。
离开时,合唱团刚好唱到副歌:“我和我的祖国,一刻也不能分割……”刘欢突然睁开眼,冲我比了个“嘘”的手指,指了指窗外——原来,不知道什么时候,隔壁摆摊的阿叔、卖花的阿姨、下棋的大爷,都站在活动室门口,跟着小声哼起来,声音不大,却像一整条老街在共鸣。
或许,这就是南宁的浪漫:不必是聚光灯下的明星,也能用歌声把一座城的温柔,唱得比邕江的晚风还绵长。而那个被街坊们称为“南宁刘欢”的老人,依旧穿着那件藏青夹克,在烟火气里,当着最普通的“歌者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