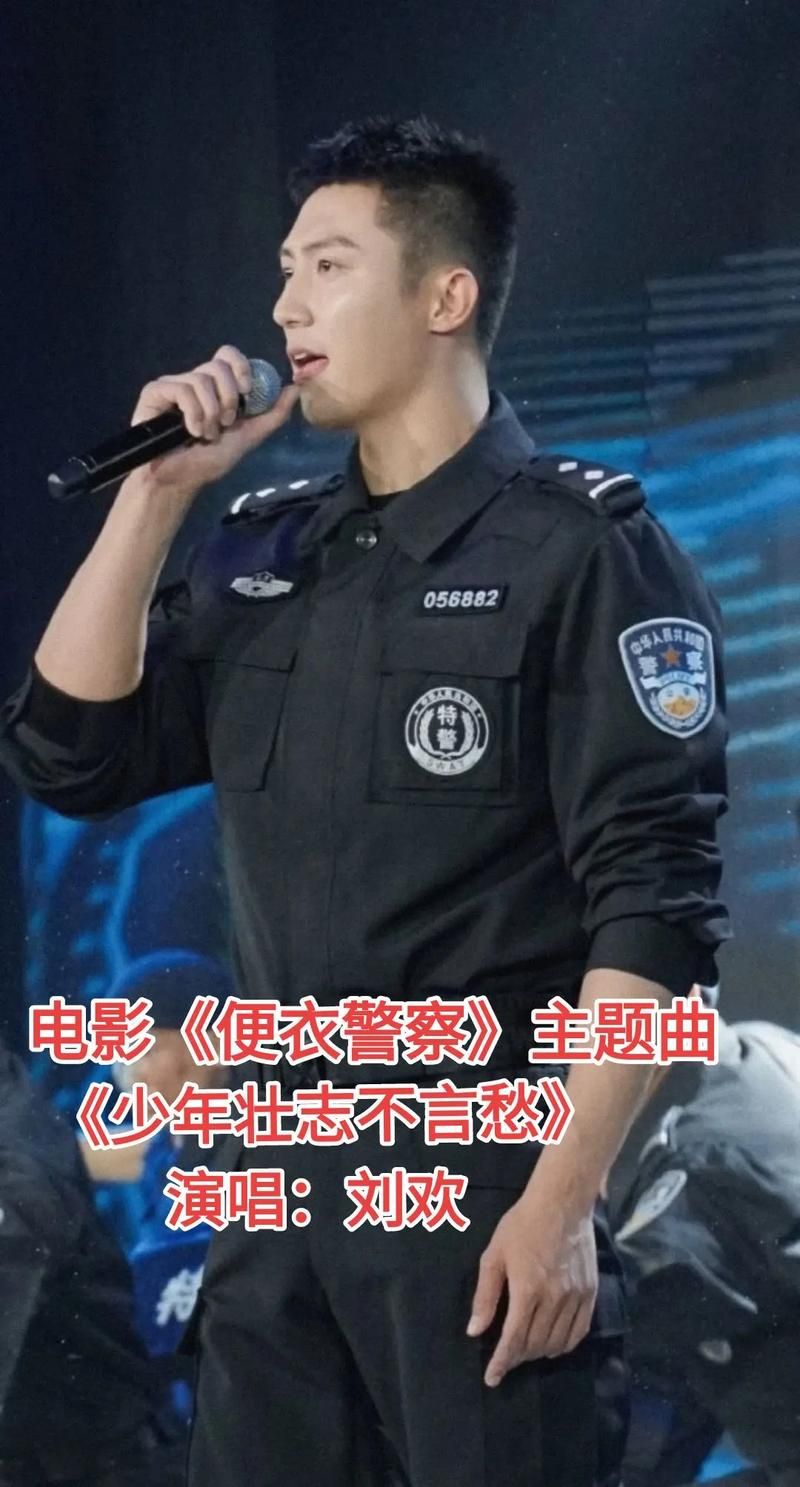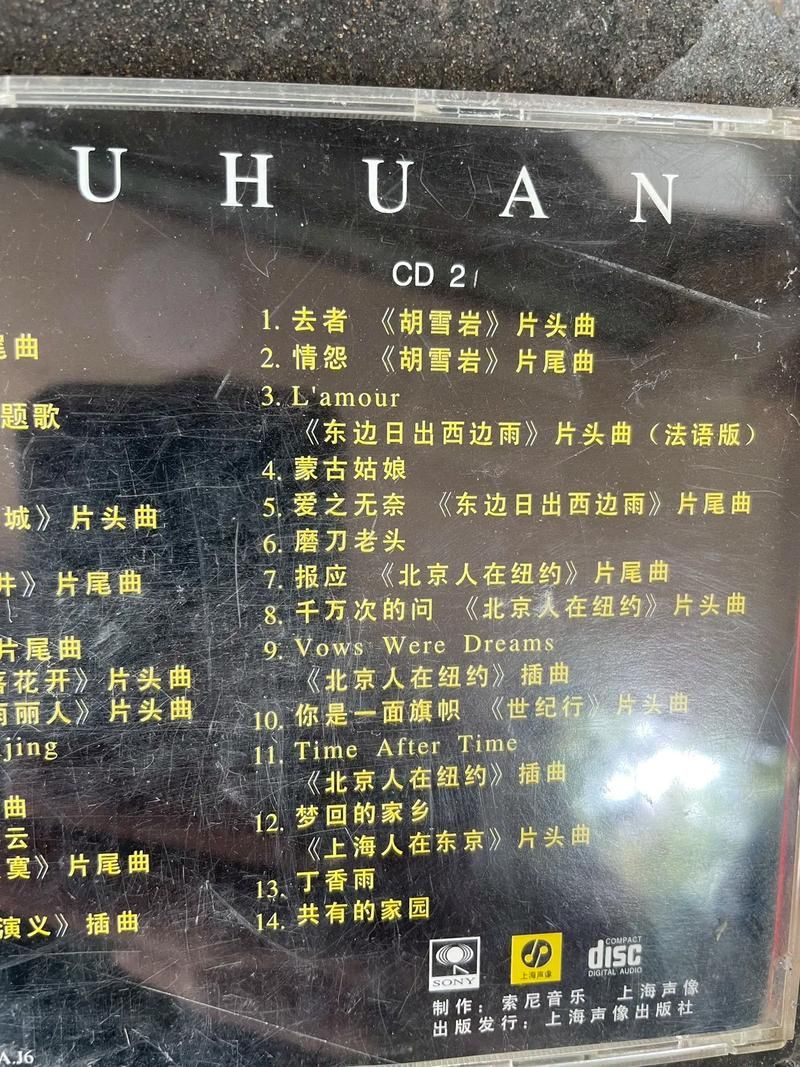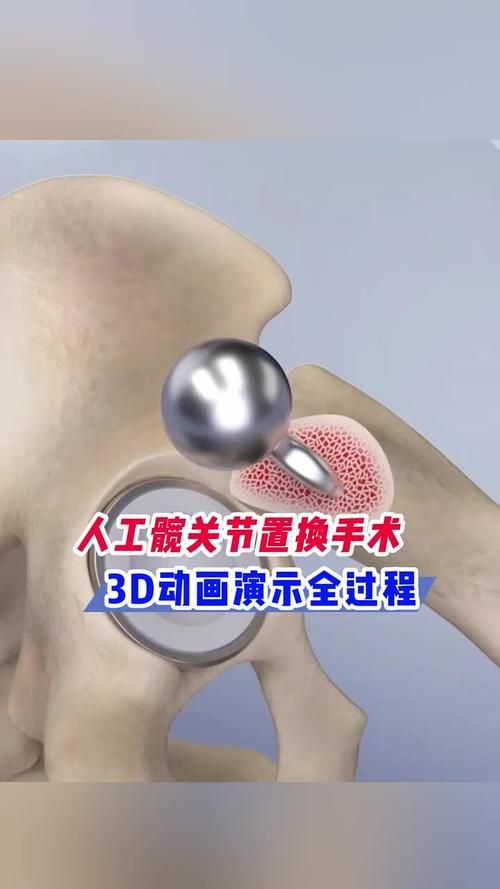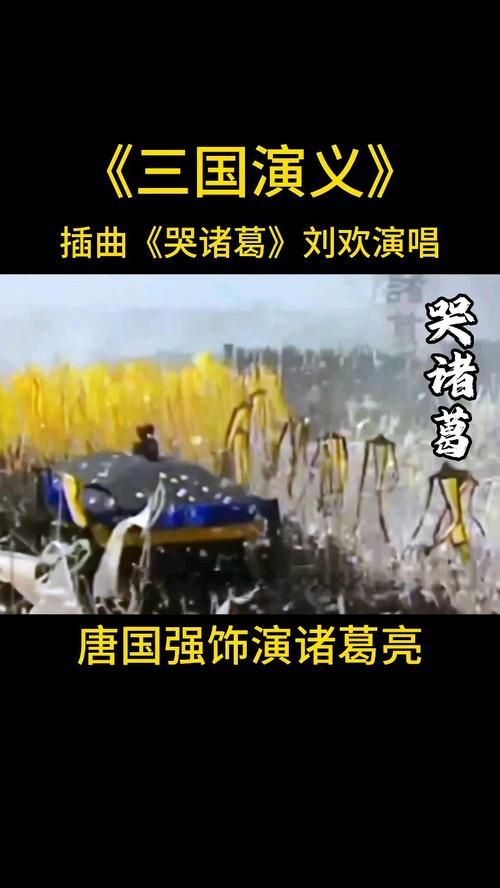最近刷短视频的你,是不是也总刷到个画面:一个穿洗得发白牛仔外套的男生,蹲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抱着木吉他,开口唱南山南时,声音像沾了胡同口的晨露,又清又透,唱到“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,走到哪里都是家”那会儿,镜头给到旁边剥毛豆的大爷,老头儿突然砸吧砸吧嘴,来了句:“这小子,比我当年在拖拉机上唱得还像那么回事儿。”
这人,就是刘欢裕。
名字带“欢”字,却总挂着副“好像谁欠他两块钱”的冷脸;有人说他是“富二代”,可看他手指缝里沾的木屑和磨出茧的指尖,又不像;更绝的是,他在采访里说:“我唱民谣不为赚钱,就为那些晚上睡不着觉的人,有个能跟着哼两句的地儿。”——这话一出,网上吵翻了:有人说他“装”,可真去听了他的livehouse,又沉默了。

从“胡同串子”到“民谣黑马”:他凭什么让高晓松侧耳?
刘欢裕的故事,是从胡同口开始的。
95年出生在北京南锣鼓巷旁边一条不知名的小巷子,家里是开老北京爆肚店的,按理说应该子承父业,可他从小就不安分。14岁那年,背着书包路过护国寺街,看见个街头歌手抱着吉他唱同桌的你,听着听着,书包一扔,蹲那儿听了一下午。回家翻出姥爷留下的那把掉了漆的旧吉他,手指头按弦按得肿成包子,愣是两周学会了童年。
“那时候我爸妈都以为我瞎胡闹,结果有天他们晚上收摊回家,听见我在店里小声唱窗外的麻雀,我妈突然就哭了——她说:‘欢裕,你唱这歌的时候,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。’”
这嗓子,算是被家里“默许”了。高中没毕业,他揣着攒了三年的零花钱,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硬座火车票,开始了“流浪歌手”生涯。在锦里大街唱成都,在宽窄巷子唱理想,在九眼桥的酒吧唱安和桥,有时候一天赚的钱不够买碗担担面,就蹲在酒吧后门跟服务员蹭点免费的米饭。
“有次在重庆,唱到凌晨两点,台下就剩三个酒鬼,非让我加唱两只蝴蝶,我说我不会,他们就把啤酒瓶子往桌上狠狠一砸,我气得抱着吉他就走了,结果刚出门下大雨,我没伞,也没钱,就坐在台阶上哭,边哭边想,我是不是不干这个。”
但真到要放弃的时候,他又舍不得。
18岁那年,他在杭州西湖边唱歌,被一个做音乐节策划的制片人听见了。制片人听完北京东路的日子的改编版,专门跑到后台找他:“你唱的民跟我听的不一样,你唱的是胡同口的烟味儿,是胡同口大爷下棋时摔棋子的动静,是胡同口卖糖葫芦的吆喝声——这个味儿,现在没人有了。”
后来,这个制片人把他推荐给了高晓松。高晓松本来只是去捧场,结果听完他唱送别,当场愣了三秒,转头对身边人说:“这嗓子,是老天爷赏饭吃啊——他唱的‘长亭外’,不是景区里表演的‘长亭外’,是真要送你走的时候,那种心里空落落的感觉。”
“我不红,正好”:这个“犟种”在较什么劲?
按理说,有高晓松背书,再蹭点综艺热度,刘欢裕早该“飞上枝头变凤凰”了。可他偏偏不。
中国好声音找过他,让他唱南山南,“导师转身肯定没跑”,但他问节目组:“我能唱我自己写的胡同里的猫吗?”节目组说:“不行,这首歌太不大众。”他直接转身就走了。
明日之子找过他,给了他一个B级评级,让他改编像我这样的人,他改成了带着京味儿Rap版本,结果播出前被节目组要求“改回原版,不然剪掉”。他二话不说,把发在社交平台上的demo删了个干净,自己跑去livehouse演。
“有人说你傻,机会不要?”采访里他挠挠头,笑了:“机会是要的,但不能丢了自己。我唱民谣,就是想说点人话,要是为了上电视,把‘胡同里的猫’唱成‘都市里的猫’,那我还不如回家爆肚去。”
就这么“犟”,刘欢裕硬是没靠综艺红了,却靠着一首首带着胡同味儿的民谣,在年轻人里“杀”出了一条路。
他在抖音上发了个北京胡同日常,视频里他拎着把吉他,边走边唱,路过胡同口卖杏仁豆腐的摊子,摊主阿姨听见是他,直接把一碗刚做的杏仁豆腐塞他手里:“欢裕,今儿不收你钱,唱得比我家老头子当年强!”视频下面有人评论:“原来北京的夏天,是吉他声和杏仁豆腐的味道。”
他在网易云上发原创南锣鼓巷的猫,歌词写“猫在房顶晒月亮,我在屋里写老歌,房东说再交不上租,就得把琴搬走”,底下有条高赞评论:“听完这首歌,我把租房合同续了三年——总得有人留着北京的老味道吧。”
更绝的是,他从来不搞“人设”。采访里问他“你觉得自己算不算网红”,他撇撇嘴:“网红?我天天蹲在胡同里,连个像样的妆都不化,算哪门子网红?我就是个唱民谣的,胡同串子。”
问他“有没有想过大红大紫”,他突然认真起来:“想过啊,但我怕红了之后,胡同口大爷不找我了,爆肚店阿姨不给我留好吃的了,那我还唱什么歌?”
“民谣不死,胡同永存”:刘欢裕的“野心”是什么?
现在的刘欢裕,早不是那个在街头混饭吃的小子了。他有了一支小乐队,有了自己的录音棚,甚至有音乐公司愿意给他投几百万,让他出专辑、开巡演。
但他还是喜欢回到胡同里。
前阵子,他在南锣鼓巷开了场小型音乐会,没请大导演,没发通知,就发了条朋友圈:“晚上七点,南锣鼓巷口老槐树下,来听歌吗?” 结果来了三百多人,有胡同里的老街坊,有特意从外地赶来的歌迷,还有几个举着相机的记者。
他唱胡同里的猫,唱到“猫啊猫,你什么时候长大”,台下一个五岁的小男孩突然大喊:“刘欢裕,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唱歌!” 他停下来,摸了摸男孩的头,笑着说:“好,那你得好好练吉他,到时候我跟你合奏。”
唱送别的时候,台下有人在跟着哼,有人在小声哭,唱完,他鞠了个躬,说:“谢谢你们,让我觉得,我这些年没白走。”
有记者问他:“你觉得什么是‘真正的民谣?”他想了想,指着旁边的胡同说:“你看这胡同,里面有四合院,有老槐树,有爆肚店,有卖糖葫芦的——民谣啊,就是唱这些东西,唱老百姓的日子,唱心里那点事儿。它不用多高级,也不用多流行,只要有人听,有人跟着哼,那就活得下去。”
现在的刘欢裕,还是会在没人的时候,蹲在胡同口的老槐树下,抱着木吉他,唱北京东路的日子,唱成都,唱他自己写的爆肚店的故事。
有人说他“固执”,可谁又能说这种固执不是一种珍贵呢?在这个所有人都想“一夜爆红”的时代,偏偏有这么个人,守着胡同里的一点“老味道”,慢慢唱,慢慢等,等那些跟他一样,心里藏着点念想的人。
所以,刘欢裕到底凭什么?
凭他不忘了自己是谁,凭他把“日子”唱进了歌里,凭他用一根弦,弹出了胡同里的春夏秋冬。
或许,这就是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