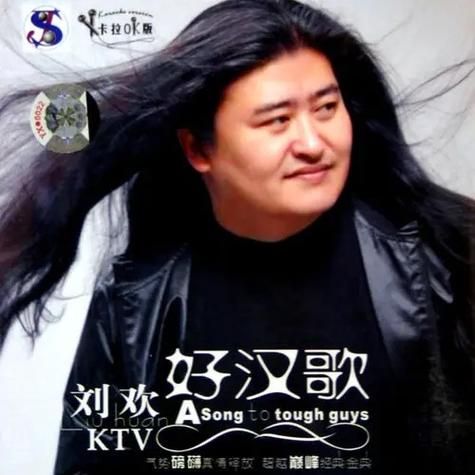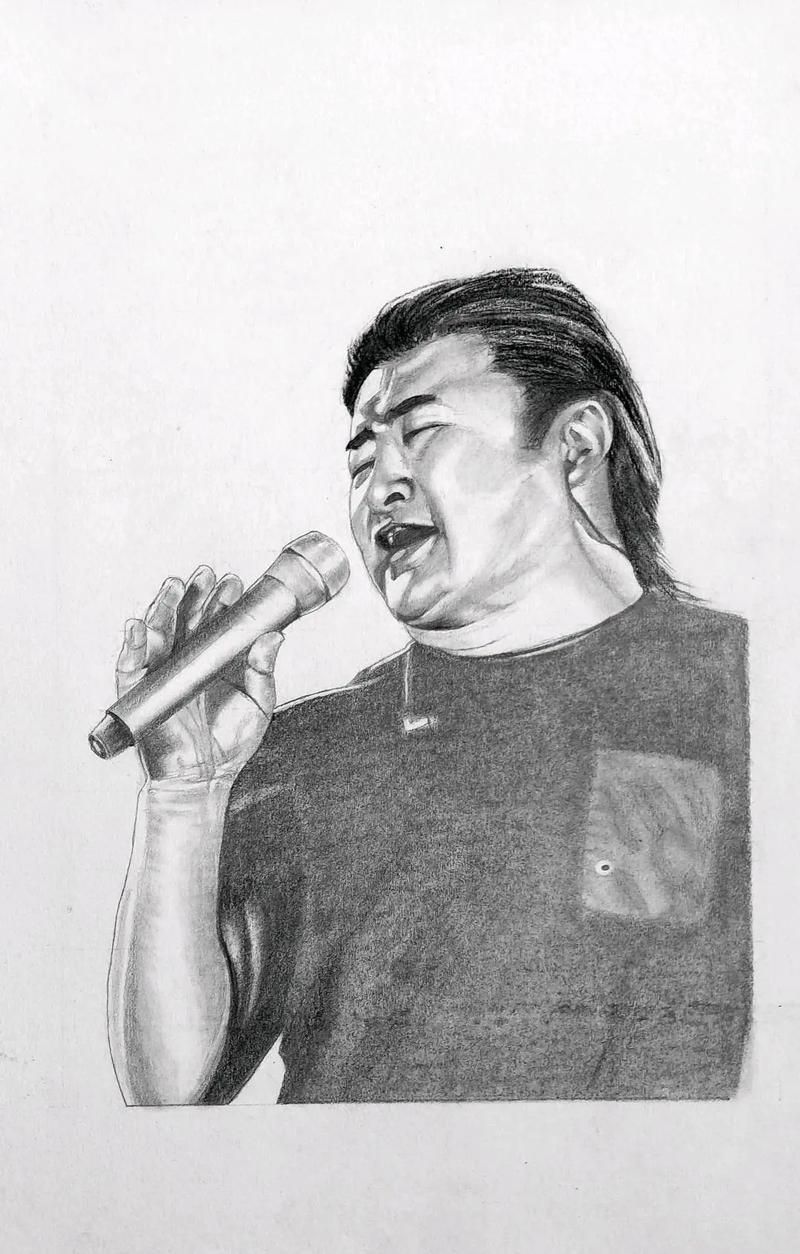在娱乐圈,提起刘欢,三个字蹦出来:前辈、实力、传奇。从少年壮志不言愁唱到好汉歌,从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到甄嬛传里的凤凰于飞,他的歌是几代人的BGM,他的嗓子被评价为“老天爷追着喂饭”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舞台上光芒万丈的歌者,同时也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系教授、研究生导师,从2004年第一次站上讲台算起,带学生这一带,就是近二十年。

你可能会好奇:刘欢的学生上课都学啥?会不会一开口就被要求“唱成弯弯的月亮那个味儿”?当“歌坛常青树”坐镇讲台,学生到底是跟对了人“躺赢”,还是得天天被“鞭策”到想哭?
“刘老师上课,不教你怎么‘飙高音’,教你怎么‘不跑调地讲故事’”

第一次走进刘欢课堂的研究生,难免有点“怵”。毕竟,课堂上坐着的这位,是能把千万次的问唱到让人起鸡皮疙瘩,也能在好汉歌里把豪迈与苍桑揉成一炉的歌者。但真正上课后,学生却常被他的一句话“破防”:“唱歌不是比谁嗓子亮,是比谁能让人听明白你在说什么。”
刘欢的教学,从不纠结于“换气技巧”“音域跨度”这些表面功夫。他更在意的是学生对音乐的理解——为什么弯弯的月亮前奏一起就能勾起乡愁?为什么昨日重现的旋律能穿越三十年让人眼眶发热?他会带着学生分析乐谱里的每一个音符:“看这里,这个半音不是随便降的,是模仿人叹气时的那种犹豫,你要把它唱出‘话’的感觉。”
有学生回忆,一次汇报演唱,他选了一首英文老歌,自以为发音标准、气息稳,却被刘欢叫停:“你把每个字都‘嚼’碎了,意思没出来。这首歌讲的是对逝去时光的怀念,你得让听众‘看见’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,而不是听你背单词。”那次之后,他终于明白:刘欢要的不是“唱歌机器”,是“会讲故事的歌者”。
“他从不让学生‘复制自己’,反而拼命推你往‘陌生’的地方走”
作为导师,刘欢最忌讳“模仿”。他常说:“刘欢只有一个,你把自己活成第二个刘欢,永远只能当‘赝品’。”他的学生里,有唱民族唱法的,有玩爵士的,甚至有做电子音乐的,风格天差地别,但刘欢总能找到每个人的“根”。
有个学生嗓音条件特别适合唱美声,一开始总想往“刘欢式”的浑厚唱法上靠,结果越唱越别扭。刘欢听后,直接给她放了黄绮珊的灯塔:“你听听,她的声音细,但力量全在咬字里,你能不能学她的‘韧’,而不是我的‘厚’?”后来,这位学生的毕业演出上,用细腻又坚韧的嗓音唱了一首冷门民谣,台下掌声雷动,她后来说:“刘老师把我从‘想成为他’的梦里拽出来,逼我看见‘我自己’。”
他还敢让学生“折腾”。有个男生想做嘻哈与中国风的融合,拿来的Demo里全是电音和快板,刘欢听完没评价好坏,反而丢给他一本宋词选:“把苏轼的定风波拆了,看看每个字的平仄,再想想怎么用节奏把它‘翻译’成现代人的话。”那段时间,男生天天泡在图书馆,从诗经到乐府诗,从古琴谱到现代编曲,最后做出的歌,把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豁达和嘻哈的自由感糅得恰到好处,连刘欢都夸:“这小子,有悟性。”
“‘赚到了’是肯定的,但‘压力’也是真的——他比你更怕你把自己耽误了”
在学生眼里,刘欢有点“矛盾”。课堂上,他可以是那个会因为学生唱错一个音就拍桌子的“严师”;下了课,却会抱着吉他给学生弹同桌的你,笑着说:“我当年在学校,也老在琴房弹这个,追女生用的。”
这种“矛盾”,其实是他藏在“严格”背后的“怕”。他怕学生急功近利,怕他们为了博眼球走捷径,更怕他们忽略音乐里最重要的“真诚”。有学生毕业后急于出圈,接了很多商演,写的歌也都是口水情歌,刘欢知道后,没有骂他,只是发了一段话:“我唱了半辈子歌,最明白一件事:能让人记住的歌,从来不是‘火’的那几天,是十年后有人听到前奏还能跟着哼的。”
现在,他的学生有的留校任教,有的成为音乐制作人,有的在原创音乐小有名气。但无论走多远,他们手机里都存着刘欢发的一段语音:“别慌,慢慢来。好东西,都‘熬’得出来。”
说到底,刘欢带研究生,哪里是在教“唱歌”?他是在教“怎么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”——懂技术,更懂人性;想成功,更想长久。当学生站在台上,唱着自己写的歌,眼里有光时,大概会真正明白:跟着这样的老师,哪里是“压力山大”?分明是“赚到了”一辈子的财富。
毕竟,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,还有人愿意花二十年时间,教学生“怎么好好唱歌”,怎么把歌“唱进心里”,这本身就是一件,像他歌声一样珍贵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