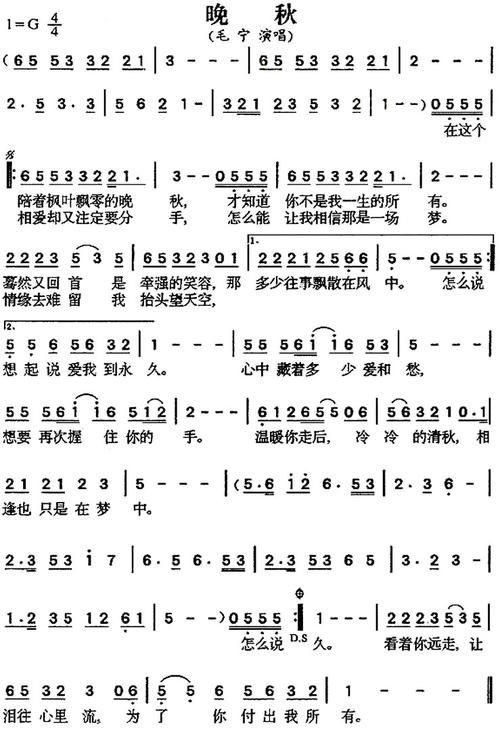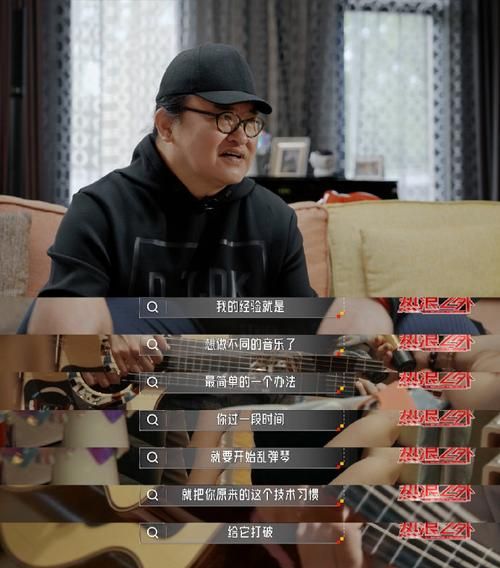提到刘欢,你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啥?是好汉歌里“大河向东流”的豪迈,是弯弯的月亮里“岁月静静地流”的深情,还是千万次的问里“可认识你吗”的苍凉?咱们总以为,这位“内地乐坛扛把子”就该端着“歌唱家”的架子,用醇厚的嗓音演绎“岁月长河”——可偏偏就有那么一首歌,让他彻底撕下“高冷”标签,成了个搂着话筒就蹦跶的“快乐大男孩”。

要说第一次听欢乐的跳吧,是十年前公司的年会。音响里突然蹦出一段手鼓+手风琴的旋律,欢快得像是草原上的风把整个会场都掀翻了。紧接着是刘欢的笑声,不是舞台上那种训练有礼的“哈哈”,而是带着点孩子气的“咯咯”,像邻家大叔喝了二两酒,非要拉着人跳新疆舞。我们总监平时严谨得像块表,那天居然跟着旋律扭起了肩膀,嘴里还念叨:“这……这不是刘欢吗?他怎么会唱这个?”
后来才扒明白,这首歌的原型是新疆民歌快乐的跳吧,刘欢在2010年的春晚联排上临时起兴,改编成了带着摇滚味儿的版本。谁也没想到,这位平时唱贝多芬、唱莫扎特,连眼神都写着“艺术崇高”的教授,居然能把民歌唱得这么“野”——编曲里加了电吉他,鼓点砸得像鼓槌直接敲在心上,他自己在台上是咧着嘴唱的,时不时还踮起脚尖转半个圈,手腕上的银镯子都跟着晃出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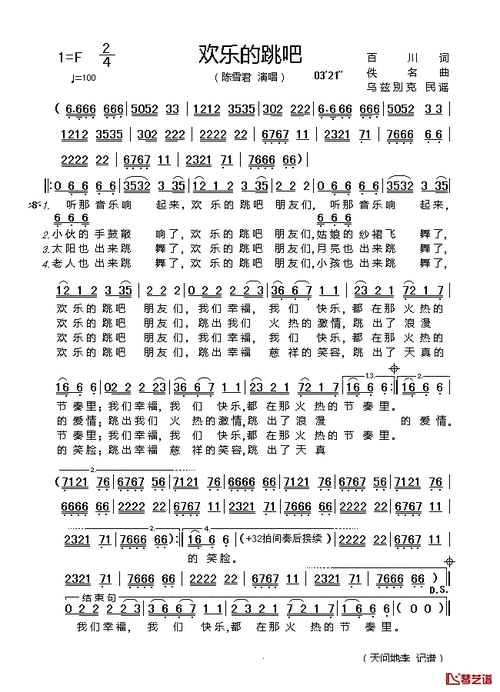
但你别以为这只是他“玩票”。听着他唱“来吧,来吧,朋友,跳吧,跳吧,朋友”,你会发现,他的嗓子完全放下来了。没有了好汉歌里的“拽”,也没有在路上里的“稳”,反倒像是在自家炕头上跟老伙计喝酒,声音里裹着热气,每个字都带着“咱们就这么乐呵”的亲劲儿。高音依旧是招牌,但不再是“为了高音而高音”,而是像手风琴的簧片突然弹起来,带着股“快乐到飞起”的劲儿,直往你耳朵里钻。
有次采访,刘欢被问到“为什么总挑这种‘不正经’的歌”,他挠头笑了:“音乐嘛,不就图个痛快?我研究了一辈子声乐,知道怎么把声音雕琢得‘高级’,但‘高级’有什么用?能让大妈们听到就想跳,能让加班的人听到就想跟着哼,这才叫‘管用’啊。”这话让我想起我妈——她平时只爱听邓丽君、蒋大为,结果每次欢乐的跳吧一响,她立马扔下择菜板,跟着电视里的刘欢扭起来,嘴里还喊:“这调子,真带劲儿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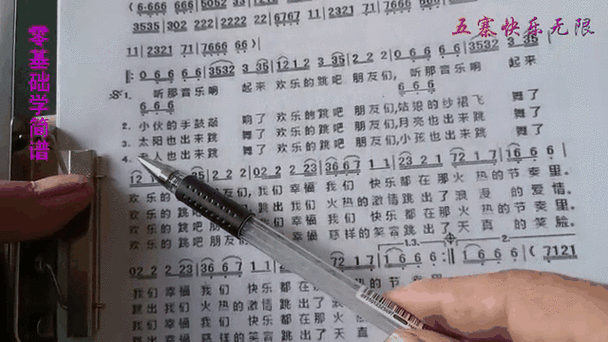
其实刘欢的歌,从来都不是“只可远观”。他唱北京欢迎你,是站在鸟巢里张开双臂说“咱家来客人了”;唱重头再来,是在低谷里拍着胸脯说“怕啥,从头来过”;而唱欢乐的跳吧,更像个孩子攥着一捧糖,非要往你嘴里塞:“你看,快乐这东西,多简单啊,不就是跟着音乐蹦跶嘛?”
你看,真正的艺术家,从来不是端着架子的“神”。就像刘欢,他能在大剧院里唱弥赛亚,也能在热闹的晚会上咧着嘴唱欢乐的跳吧——因为他知道,音乐的本质从来不是“多难”“多高级”,而是能不能让人跟着动起来,让心里那点灰,被手鼓声一扫而空。
所以啊,下次再听到欢乐的跳吧,不妨跟着扭两下。毕竟,能让刘欢“放下身段”这么玩的快乐,可不是天天都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