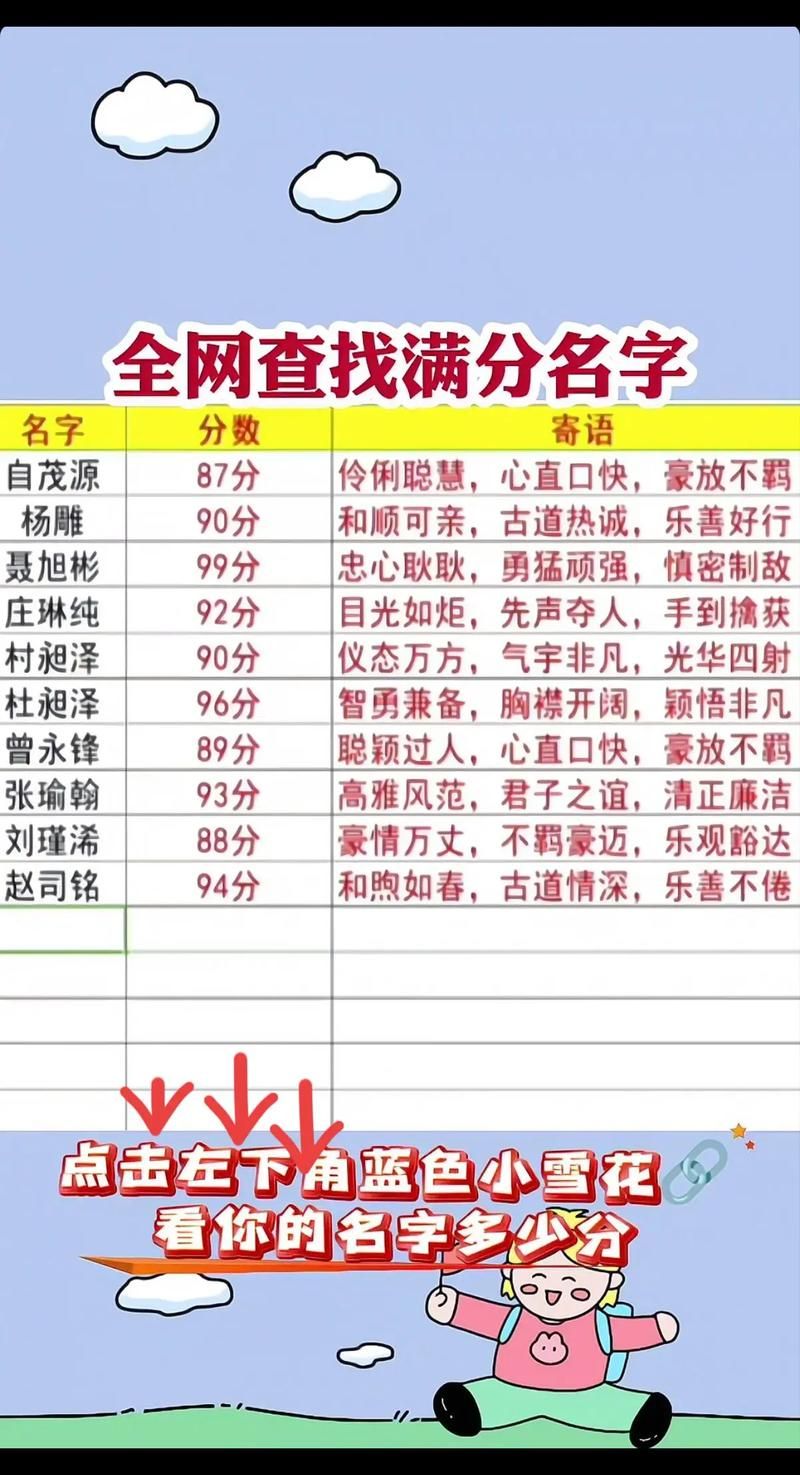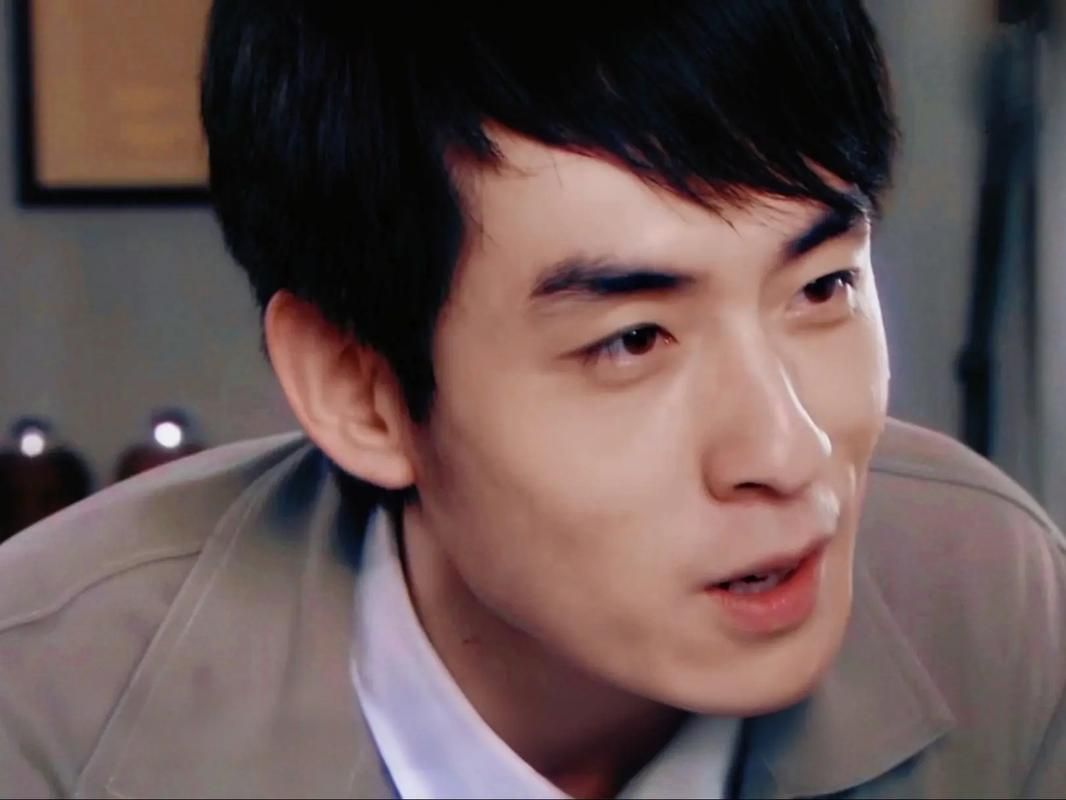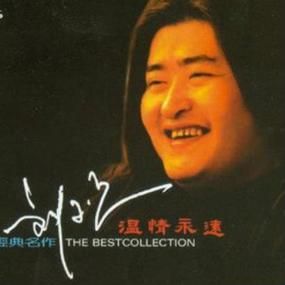上回和朋友在KTV,点到好汉歌时,音响里的刘欢一句“大河向东流”刚起,包厢里顿时跟唱声一片。有人笑着摇头:“这歌都多少年了,怎么还是一开口就上头?”后来有人点了龙的传人,前奏一起,王力宏的“遥远的东方”一出来,半个包厢都跟着和音;直到谭维维的华阴老腔一声喊响起来,那句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”,愣是把唱情歌的气氛唱成了“全村最靓的仔”——那一刻突然发现,好像不管过多少年,只要这三位一开口,总有种魔力,能让人跟着旋律摇,跟着歌词走。

这魔力到底在哪儿?是技巧?是阅历?还是他们唱的从来不只是歌?
先说刘欢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他唱歌时那个经典动作:闭着眼,微微仰头,手掌在半空里随着节奏轻轻划拉。以前总觉得是“舞台范儿”,后来听他一次采访才明白,那是“把自己交出去”的状态。他唱千万次的问时,不是在“演”痛,是真把故宫的红墙绿瓦都唱成了思念的背景;唱从头再来时,那声“心若在梦就在”不是喊出来的,是从喉咙里压出来的,像中年男人拍着桌子说“我可以”。

很多人说刘欢“唱得太满”,可你听好汉歌里“路见不平一声吼”,那吼声里哪有什么技巧,就是一个普通人看到不公时的仗义;弯弯的月亮里“我的心充满惆怅”的惆怅,又哪里是刻意煽情,就是中国人对家乡最朴素的牵挂。他就像个“音乐的匠人”,不标新立异,却把每一个字都磨成了能钻进人心的钩子。记得中国好声音带学员时,有位学员唱得花里胡哨,刘欢直接打断:“你把歌词吐清楚,比什么都强。”对他来说,歌是“传情达意”的工具,不是炫技的玩具。
如果说刘欢是“沉下来”的厚重,那王力宏就是“跳出去”的巧劲。他刚出道那会儿,总被说“偶像派”,可谁又能想到,这个会弹钢琴、会写歌、会跳街舞的年轻人,后来会成了“华语Chinked-out之父”?
你听龙的传人,前奏还是传统的琵琶声,到副歌突然切进Rap和摇滚,像个穿着长衫的小伙子突然蹬上了滑板,又酷又协调;盖世英雄里,京剧念白和电子乐混搭,让外国人都跟着喊“嘿!嘿!嘿!”。他像玩魔方的高手,把R&B、Hip-hop、中国风这些七零八落的元素,拧成了独一份的“王氏风格”。
但比风格更绝的,是他的“较真”。有次看他的纪录片,写你不知道的事时,为了一个和弦反复录了上百遍,钢琴弦都弹得发烫;唱需要人陪时,他不追求高音,就挑着气声唱,像凌晨三点在电话这头小声哭的男孩——原来他不是不会“柔软”,是总在琢磨“用什么样的声音,才能说出你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”。
到了谭维维,这姑娘简直就是“打破边界”的代名词。很多人认识她,还是从2006年梦想中国的亚军开始,那时她唱的往日时光干净得像山涧里的泉水,谁能想到,十年后的她会和华阴老腔的老爷爷们站在台上,吼出一声“一声喊就唱得那黄河水倒流”?
记得第一次看中国之星上她唱华阴老腔一声喊,前奏还是安静的小提琴,突然一声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”炸出来,我手里的筷子差点吓掉了。不是夸张,那声音里有黄河的浪、黄土的厚、庄稼人的倔,像从秦岭深处刮来的风,把“流行”和“传统”的墙吹得稀碎。后来她唱带灯,把陕西信天游的哭腔揉进旋律里,唱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时,眼里闪着光,不是“要证明自己”,是“凭什么女子就不能活出自己的样子”。
她像株带刺的玫瑰,初见时以为是温室里的,后来才发现,早把根扎进了民间的泥土里。有人说她“转型太大胆”,可她总笑着说:“音乐的根还在土地里,长出来的叶子才不会发黄。”
所以你看,刘欢的“实”、王力宏的“巧”、谭维维的“野”,明明是三种完全不同的路,为什么都能让我们心服口服?
可能因为他们唱的从来不只是“歌”。刘欢唱的是岁月里的故事,像父亲抽着烟时讲的过往;王力宏唱的是年轻人的闯劲,像哥哥拍着你肩头说“试试看”;谭维维唱的是土地里的力量,像奶奶哼着童谣哄你睡觉的歌谣。
好的音乐不就是这样吗?它不管你听没听过几首歌,不管你懂不懂什么技巧,它就那么轻轻地,落在你心里最软的那个地方,让你跟着高兴,跟着难过,跟着觉得“啊,原来也有人懂我”。
所以下次再听到刘欢、王力宏、谭维维唱歌,别急着评判“唱得好不好”,不如闭上眼听听——他们唱的,或许就是你心里那首没说出口的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