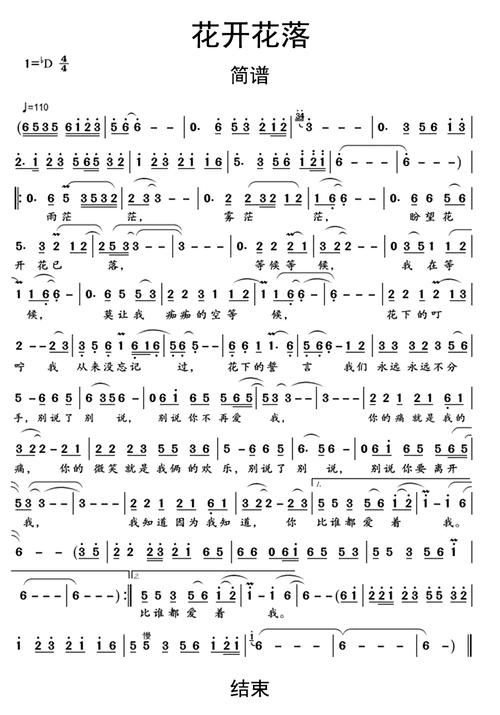那天晚上,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刚暗下来的场灯,突然被一片手机闪光灯点亮——像撒了满天的星星。舞台中央,刘欢穿着一件深蓝色对襟褂子,话筒举到与肩齐高的位置,喉结动了动。前奏响起的第一秒,我听见旁边有人闷着嗓子喊:“这是要州的调子啊!”
接下来三分钟,全场三万人跟着他唱,从“踏遍要州山水路”到“雄风万古留声”,有人把嗓子唱劈了,有人抹着眼泪挥舞荧光棒。有人后来在社交平台写:“活了三十年,第一次为一首歌红了眼眶,不是因为词多好,是刘欢唱那声‘雄’字时,我突然想起爷爷说的,要州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”
要州雄风这首歌,大多数人可能没听过名字,但只要前奏一响,要州人准能竖起耳朵——它不是什么流行神曲,是要州本地艺人在传统小调基础上改编的新作,词里写要州的茶马古道,写长江边的船工号子,写老城墙砖上的刀刻斧痕。原本只是地方台春晚的小节目,却被刘欢在一次音乐节上“捡”了来,改编成了交响乐版,没想到一火再火。

有人问:“刘欢都这岁数了,怎么还唱这种‘地方小调’?” 可要州人摇头笑:“这不是小调,是咱的根。”
去年要州文旅局的人去北京请教刘欢,说要想让年轻人了解家乡文化,得找“流量歌手”唱流行改编。刘欢当时正翻着要州的老曲谱,头也没抬:“流量像流水,流过去就没了。真正能扎根的,得是这片地里的种子。你们听过要州船工拉纤时的‘哦嗬号子’吗?那调子起起伏伏,和黄河边的信天游一样,是人在跟山水较劲儿,也跟命运较劲儿。”
他真把要州雄风往“种子”里做。交响乐团编曲时,特意加了段编钟,说“要州古时候是楚国地界,编钟一响,魂就回来了”;录音时他反复练那句“大江东去浪淘沙”,声音从低沉到高亢,“就像船工从弯腰拉纤站直了腰杆,得有股劲儿往上顶”。后来这首歌成了要州文旅的宣传曲,不光本地人听着亲切,连外地游客说:“听完就想去要州看长江边的古栈道,看看歌词里写的‘雄风’到底是什么样。”
刘欢的演唱会,从来不是“个人秀”,更像是一场“老物件焕新”的集体回忆。他唱好汉歌,会把山东快书的节奏加进去,台下大爷大妈跟着打拍子;唱从头再来,会提到自己年轻时在歌厅跑场的经历,“那时候唱十首歌,观众可能只记住一句,也得用心唱”。这次唱要州雄风,唱到“老城墙头望月光,谁家灯火照归乡”时,他突然停下来,清唱了一句——没话筒,没伴奏,清亮亮的声线裹着砂砾感,像小时候趴在爷爷膝头听他唱的童谣。
“那天晚上,场灯暗下的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为啥三万人会跟着唱。”一位看完演出的大学生写了篇长文,“刘欢不是在‘表演’这首歌,他是在替我们说那些没说出口的:对家乡的惦记,对传统的敬畏,对‘我们是谁’的追问。他说音乐要‘见人见景见文化’,原来最厉害的‘雄风’,从来不是多大的声,是能扎进人心里,跟着呼吸一起颤动的那股劲儿。”
你看,真正的“雄风”,从不是震耳欲聋的呐喊,是刘欢唱“雄风万古留声”时,眼里那点不灭的光——那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,是年轻人心里藏着的文化火种,是这片土地上,谁也夺不走的心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