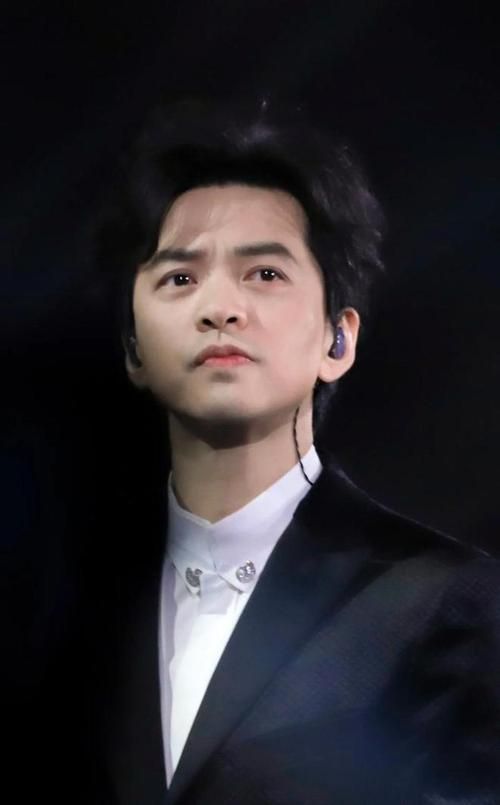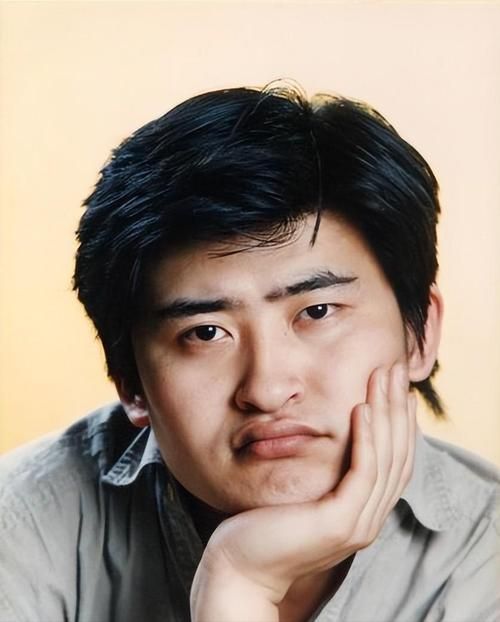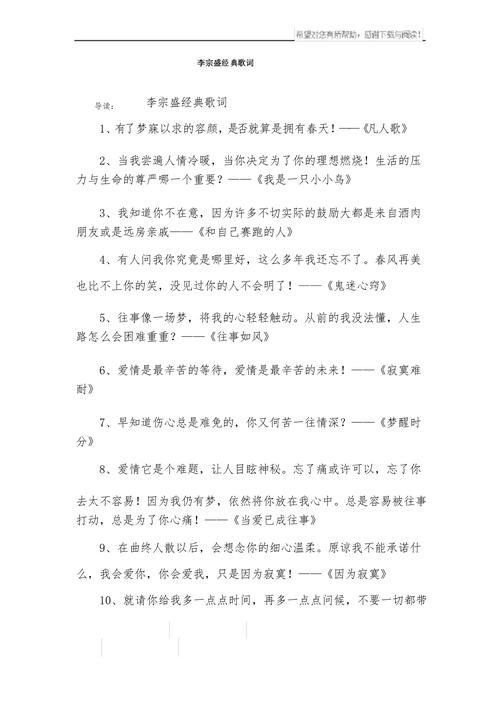刘欢的声音,总像陈年的老黄酒,初入口觉得醇厚,咽下去才发现,里头藏着整个江湖的滋味。他不唱风花雪月的矫情,偏爱把土地的厚重、远行的孤勇、归途的渴望揉进旋律里,让每个听的人,像撞进了自己的心事里。
最近后台总有人问:“刘欢有没有一首歌,是专门写离家的?” 我翻出他所有的专辑,最后停在2018年为“乡土中国”公益项目写的远行的帆上。开头那句词,像一记轻锤,突然就敲在无数人的心尖上——“你可是骑乘过故乡的月亮,把炊烟折成船票,飘向未知的渡口。”
起初听,只觉得画面感强。可细想,“骑乘故乡的月亮”,哪是简单的“走过”?那是小时候爬上屋顶,以为踩着月光就能摸到星星的傻气;是临行前,娘在灶前添柴,火光映着她的白发,你低头数着鞋尖的土,不敢抬头看她通红的眼睛。刘欢后来在采访里说,这个词他琢磨了三天,就想找个既有“离开的决绝”,又有“被故乡托着走”的温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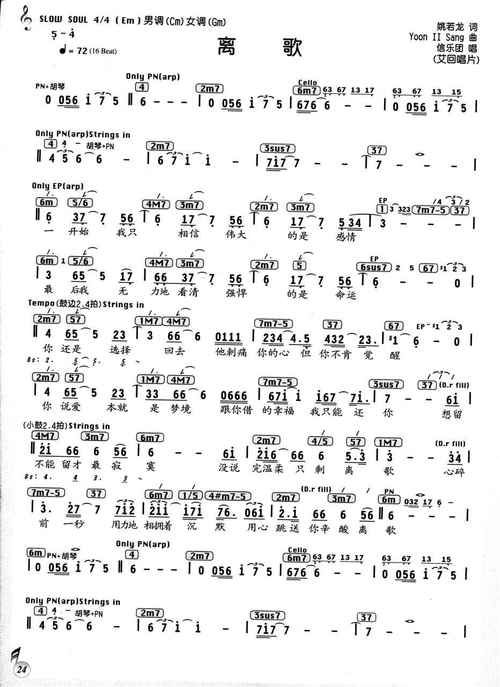
2018年他去山东济宁采风,遇到个七十多岁的老汉蹲在村口晒麦子。问他:“娃在外打工,不想?” 老汉磕了磕烟袋,火星子溅在脚边:“想,可娃得闯。咱这土里刨食的,供不起啊。”那天晚上,刘欢住在村招待所,窗外没月亮,只有后山风刮过玉米地的声音,沙沙的,像娘的低语。突然,他就想起自己18岁揣着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,爹在车站递给他一个布包,里头是五个煮鸡蛋,还有张写着“吃饱饭,别想家”的纸条。
远行的帆里,他刻意没写“苦”。写“炊烟折成船票”,是想起娘临走前,往他布包里塞的烙馍;写“未知渡口”,是说儿时总以为远方是金山银山,真到了才发现,不过是租十平米的地下室,吃泡面配火腿肠;写“回头望”,是深夜加班,地铁穿过隧道时,突然想起村里的狗叫——那狗叫有多吵,家就有多温暖。
深圳的程序员小陈,有次加班到凌晨三点,耳机里循环这首歌,突然哭了。他说,来深圳第五年,没回过家。妈总说“不忙就不回”,可前两天视频,背景音里邻居问“你家小陈今年过年回来吧”,妈慌忙说“回,肯定回”,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。杭州的小林,大学毕业在杭州落脚,毕业典礼那天,和室友在宿舍喝酒,放这首歌,男生们红着眼圈唱“我们曾是孩子,把天涯当故乡”——原来每个离家的人,都是举着“故乡”当盾牌,在异地磕磕绊绊长大的孩子。
刘欢自己,算是最懂“离家”的人。从山西阳泉到北京,一走就是四十多年。他说:“离家的歌,不是唱给别人听的,是唱给每个‘假装坚强’的自己。你嘴硬说‘不苦’,却会在听到一句‘吃饭了吗’时,突然破防。”
去年他在“声生不息”的舞台上唱这首歌,没加华丽的编曲,就一把吉他,像和老友聊天。唱到“船票已经被风揉皱,渡口的名字生了锈”,他顿了顿,轻轻吸了下鼻子。台下有人举着手机拍,有人捂着嘴哭——原来真正的共鸣,从不需要刻意煽情,只是把你的故事,唱成他的歌。
这世上没有“无家可归的人”,只有“在心里给故乡留着座”的人。刘欢用这首歌告诉我们:离家不是背叛,是为了把故乡的月光,揣进兜里,照亮更远的路。下次当你走在异乡的街头,突然听见那句“骑乘过故乡的月亮”,不妨抬头看看——那月光,可能正和你家乡的月亮,是同一个模样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