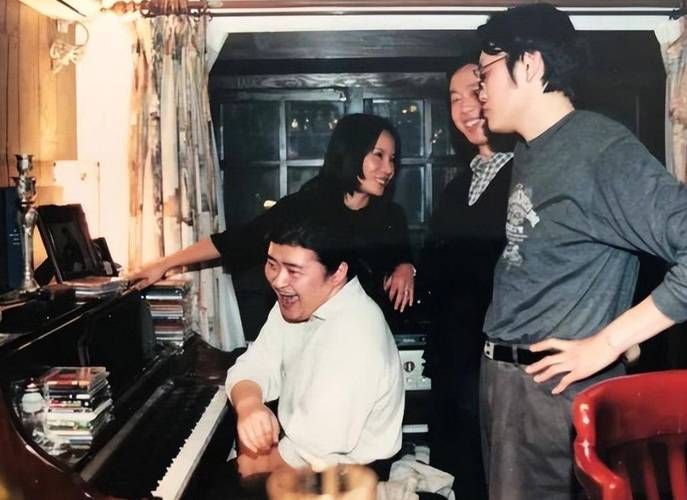2016年的中国新歌声后台,导播举着“准备下一组”的牌子时,刘欢正往保温杯里续热水。耳机里突然传来一阵略带沙哑却极具穿透力的彝族民歌,他手里的杯子顿在半空,抬头问导演:“刚才唱的是哪个队?大西南那边的?”

“刘欢战队,吉克隽逸。”
刘欢眼睛一亮,放下杯子就往舞台侧幕走:“等下,我再去听听——这嗓子,像沾着露水的云,又像山涧里蹦出来的小鹿,太有东西了。”

那个让见惯国际大师的刘欢都“挪不动步”的彝族女孩,就是后来被圈内人亲切叫“小川”的吉克隽逸。人们总说“刘欢战队是‘音乐清流’”,可鲜少有人知道,这个藏龙卧虎的战队里,小川究竟凭什么成了导师心中的“特殊存在”?
从“野路子”到“准歌者”:刘欢教会她的,不止是技巧
初登新歌声舞台时,小川的演唱带着浓重的“野生感”——高音能冲上云霄,低音又沉得像山谷的回响,但转音不够细腻,甚至有些“用力过猛”。当时其他导师都在纠结“选还是选”,刘欢却直接按下按钮,转椅刚转过来就笑着说:“你这不叫‘选’,叫‘捡到宝’了。”
后台化妆间,小川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发愣,她知道自己“野”,可也怕“野”到最后被淘汰。刘欢推门进来时,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歌谱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:“这里别喊,用气声,像跟阿妈说悄悄话”“副歌得有个‘钩子’,让听众心里痒痒的”。
“你唱歌,像彝族人背柴,劲儿使得太足。”刘欢泡了杯茶推给她,“但好歌不该是‘扛重活’,得是‘讲故事’。你听——”他打开手机,放了一段自己老录音,是首没人知道的四川民谣,“当年我录这个,录了27遍。不是技巧不行,是想把爷爷唱给我的‘调调’,用你们能懂的方式传下去。”
后来那首我是歌手舞台上的爱情,小川唱到“原来你才是我,最重要的决定”时,眼角有泪光。后台有人问她“是不是太紧张了”,她摇摇头:“是刘欢老师说,‘别当歌手,当个说故事的人’。那天我唱的时候,好像看见阿妈在火塘边织布,风从木缝里钻进来,带着松香的味道。”
刘欢战队的“特殊待遇”:她凭什么让导师“破例”?
比赛进行到“导师考核”阶段,小川抽到一首英文歌I Have Nothing。当时的她,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,急得在楼梯间掉眼泪:“老师,我能不能唱首彝语歌?”
刘欢却把歌谱折成纸飞机,扔给她:“怕什么?当年我在美国学音乐,连‘谢谢’都说不好,现在不也照样唱?这样——你先给我唱两句彝语版的,我帮你把英文‘嚼碎了’揉进去。”
后来那场考核,小川用彝语开场“阿普笃慕”(彝族创世始祖的名字),接着转入英文主歌。刘欢坐在台下,跟着节奏打拍子,眼睛里的光比舞台还亮。唱完后,其他导师都站起来鼓掌,那英笑着喊:“刘欢,你这战队藏了个‘小精灵’啊!”
可很少有人知道,为了让小川练好英文发音,刘欢连续一周每天陪她熬夜到凌晨。从“thank you”到“forever”,从纠正“th”的舌尖音,到教她用“叹气”的感觉唱长音。有次小川累了趴在桌上睡着,刘欢脱下西装外套盖在她身上,转头跟导演说:“镜头别拍她休息,拍她练歌的样子——你看她手指头在桌上敲节拍,睡着了都忘不了。”
这种“破例”,在刘欢战队里并不罕见。他会为了小川的彝族服装跟造型团队“吵架”,说“别给她穿太闪的,要让她像山里来的姑娘”;会偷偷把自己珍藏的老唱片塞给她,说“听听这个,你的根在这里”;更会在她被淘汰边缘时,在后台弹着钢琴唱凤凰于飞,说“你不是走了,是带着咱们的歌,飞去更高的地方了”。
十年过去,小川终于成了刘欢口中的“说故事的人”
如今的吉克隽逸,早已不是那个“靠嗓子吃饭”的新人。从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唱我用所有报答爱时的眼神坚定,到声生不息里把死了都要爱唱出彝族海菜腔的惊艳,再到最新专辑里用彝语、汉语、英语混搭创作的阿嬷的谣,她终于活成了刘欢当年说的“说故事的人”。
去年她参加一个音乐节,后台遇到刘欢。刘欢站在台下听了三首,上台时递给她一串红玛瑙项链:“你阿妈给你的吧?”小川点点头,眼眶红了:“老师说,人不能忘了根。”刘欢拍拍她的肩:“根扎得深,树才能长得高。你现在是‘小川’,以后要做‘大川’,把彝家的歌,唱给全世界听。”
有人说“刘欢战队是‘非冠军’的福地”,因为他的学员总是走得更远、更稳。可小川的故事或许能说明答案:刘欢看重的从来不是“技巧多厉害”,而是“心里有没有东西”。就像他当年对小川说的:“你不需要成为第二个谁,你只要成为‘第一个吉克隽逸’就够了。”
如今回看新歌声里那个穿着民族服装、带着些许怯场的彝族女孩,忽然明白:刘欢战队的“宝藏”,从来不是那些炫技的高音,而是像小川这样——带着泥土的芬芳,带着山野的风,用最纯粹的热爱,把“根”唱成歌的人。而你猜怎么着?现在的小川,真的成了那个“让世界停下来听”的歌者。
毕竟,真正的好音乐,从来都不是“选”出来的,而是“等”来的——等一个懂你的人,告诉你“别怕,你天生就该唱歌”;等一个有根的人,把歌里藏着的故事,一代代传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