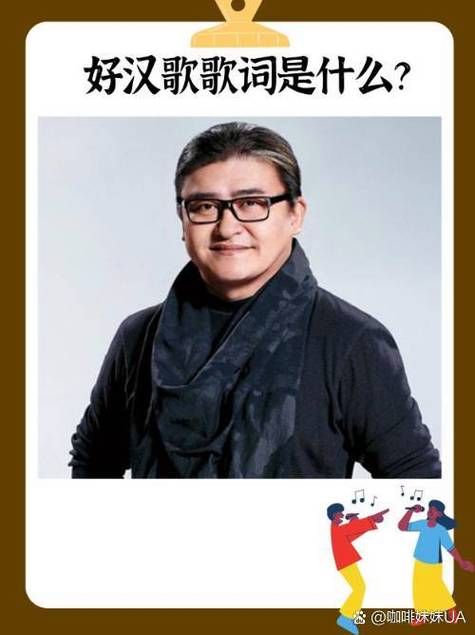提起刘欢,大多数人脑海里会立刻跳出好汉歌里“大河向东流”的豪迈,好大一棵树里的深沉,或是弯弯的月亮里的温柔。作为华语乐坛的“常青树”,他的嗓子仿佛被岁月镀了金,每一个音符都透着故事感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这位如今站在“音乐殿堂”顶级的歌者,年轻时竟有过一段“迷彩岁月”——他曾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兵,而这段看似“与音乐无关”的经历,恰是塑造他艺术人生的重要一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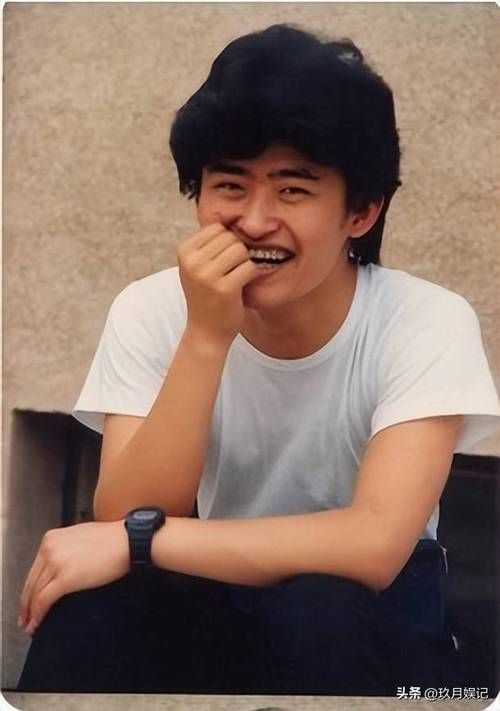
18岁的“文艺青年”,为何走进军营?
时间回到1981年,18岁的刘欢刚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,还没来得及适应大学生活,就面临人生的一个重要岔路:当时国家有号召,青年学生可以报名参军,文艺特长生有机会进入部队文工团。

“那时候哪懂什么‘职业规划”,刘欢后来在采访里笑谈,“就是觉得唱歌有意思,还能穿军装,挺神气的。”他自幼热爱音乐,中学时就开始学钢琴、练美声,在学校里是小有名气的“文艺骨干”。加上他外形高大、性格开朗,很快就被第二炮兵文工团(现火箭军文工团)的招兵老师相中,成了部队里的一名“文艺兵”。
说起来,当兵在当时的年轻人眼里,是既光荣又“吃苦”的差事。刘欢入伍后,先是在河北保定的新兵连开始了三个月的“魔鬼训练”:每天清晨五点起床,越野五公里,然后是队列训练、投弹、射击,晚上还要政治学习、写思想汇报。“最怕的是紧急集合,”他回忆,“半夜哨子一响,得在3分钟内穿好衣服、打好背包、扛上枪跑操场,有一次急匆匆把被子裹成了‘卷饼’,还被班长骂了一顿。”

但训练再苦,也没磨灭他对音乐的热爱。新兵连结束后,刘欢凭借出色的嗓子和音乐功底,被调入了文工团的演唱队。从此,他的“军营日常”变成了“半军半艺”:上午跟着部队操练、学习政治,下午则泡在琴房里练声、学乐理,晚上还要跟着队伍下基层慰问演出,有时去偏远山区,连口热饭都吃不上,但台下的战士和村民跟着唱得比他还起劲儿。
军营里的“淬炼”:不是所有兵都去扛枪
很多人对“当兵”的印象,是摸爬滚打、站岗放哨,但对文工团的兵来说,“战场”在舞台上,“武器”是麦克风。刘欢在部队里没怎么摸过真枪实弹,却用歌声“武装”了无数人心。
那时候,文工团的演出任务特别重,几乎每周都要下部队、去工地、进矿山,有时一天要赶两场演出。有一次去西北导弹基地,零下十几度的天气,他和战友们在露天舞台上唱打靶归来军中绿花,唱到最后嗓子冒烟,台下的战士们却齐声喊“再来一个”!“那一刻突然觉得,唱歌不光是自己的爱好,更是给战友们打气的事儿。”刘欢说,这些经历让他明白,“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‘花瓶’,得扎根生活,才能有温度。”
在部队,他不仅学会了“把歌唱进战士心里”,更重要的是锤炼了性格。以前他是个有点“散漫”的文艺青年,到了部队这个“大熔炉”,遵守纪律、服从安排成了本能。“班长说‘军令如山’,说一就不能有二;战友们说‘集体荣誉高于一切’,排练时谁都不能掉链子。”这种“严于律己”的习惯,后来也贯穿了他的整个音乐生涯——对待录音,他可以为一个音反复录几十遍;对待演出,哪怕重感冒也要坚持登台,用他话说:“舞台就像战场,不能‘临阵脱逃’。”
从“军营歌手”到“乐坛常青树”:迷彩服里走出的“国民歌王”
1987年,24岁的刘欢脱下军装,回到了校园,但军营的印记已经刻进了他的骨子里。后来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,成了该校第一位流行音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,再后来凭借弯弯的月亮千万次的问等歌曲火遍大江南北,成了华语乐坛的“定海神针”。
每当被问及“军营经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”,他总会笑着说:“让我学会了‘脚踏实地’。”很多人觉得他的歌声“有厚度”“有力量”,其实这正是军营给他的礼物——那些在基层演出时,看到战士们坚毅的眼神、听到工人们铿锵的号子,都化作了歌声里的“筋骨”。
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,成名后的刘欢从未忘记“老本”。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演唱世界一家,到后来为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历史大戏配乐,他的作品里总透着一股家国情怀和英雄气概,这和他当年在军中文工团唱的那些“主旋律歌曲”,一脉相承。去年有媒体拍到他在小区遛弯,穿着朴素的夹克,路过广场舞大妈的音响,看到她们在唱好汉歌,他竟笑着跟着哼了起来,还主动和大妈打招呼——比起“歌王”的称号,他更像个“从部队里回来的老大哥”。
如今,刘欢已经年过六旬,很少出现在综艺舞台上,但只要有他献唱的场合,总能掀起回忆杀。有人问他“还会再唱好汉歌吗”,他总是点头:“当然,只要战友们、听众们爱听,我就一直唱下去。”
你看,从18岁的迷彩小兵,到如今的国民歌王,刘欢的人生就像一首“进行曲”,每一个节拍都带着军营的铿锵,又融着人间的烟火。下次再听到他的歌声,或许你会想起:那个在训练场上跑得气喘吁吁的少年,那个在聚光灯下用歌声征服观众的歌者,最初的他,也曾是个把“为人民服务”刻在心里的普通士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