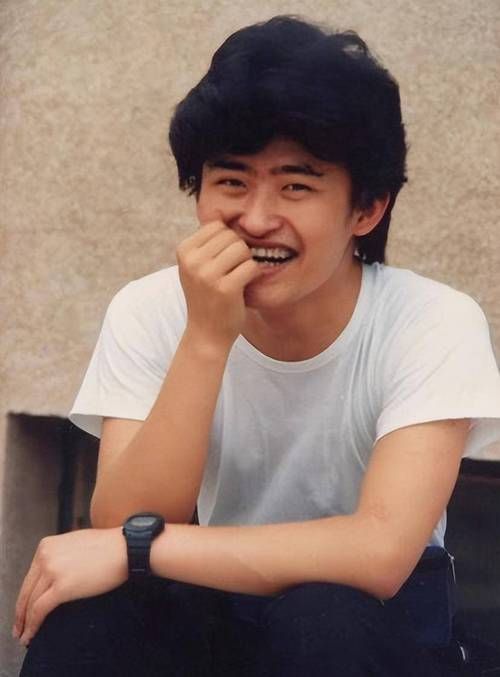今年初秋,天津某社区公园的清晨,几个晨练的大爷正围着棋盘杀得酣畅,突然邻树传来熟悉的男中音:“哟,这马敢跳卧槽?您这棋艺可退步啊。”抬头一看,穿灰色帽衫、踩旧布鞋的不是刘欢是谁?他没带助理,手里拎着豆浆油条,正笑呵呵地看着棋局——这画面,天津老百姓早见怪不怪了。从1987年第一次踏上天津的土地算起,刘欢和这座城市的缘分,早就像煎饼果子的薄脆儿一样,又脆又香,嵌进了彼此的骨子里。

天津土味的“音乐启蒙”:澡堂子里听来的梆子腔
很多人不知道,刘欢的“音乐第一课”是在天津的澡堂子里上的。他7岁那年跟着父亲来天津探亲,住在和平区五大道的一处老洋房里。邻居是个唱京剧的“老戏迷”,总爱在澡堂子里泡着,扯着嗓子唱铡美案的“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”。“那澡堂子蒸汽腾腾的,他的声音穿云裂石,我当时就觉得,这比收音机里的戏好听多了!”刘欢曾在一次采访里笑言,“后来才知道,那是天津卫最地道的‘卫梆子’,带着股子不服输的硬朗劲儿。”

这股“硬朗劲儿”,也刻进了刘欢的音乐里。1986年,他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,把第一份工资寄给了在天津工作的姑姑,托她买了张津门特产曲艺选的磁带。里面有骆玉笙的剑阁闻铃,有马三立的逗你玩,还有他最爱的天津快板——武松打店。他后来跟学生聊起这段:“你们不懂,天津曲艺里的‘说学逗唱’,不是死板的技巧,是‘天津人过日子得找乐儿’的劲儿。后来我写千万次的问,那句“千万里千万里,我追寻着你”,里头就藏着天津快板的节奏——明快的底下,是憋着的一股韧劲。”
从“郎朗铁哥们”到“天津姥爷”:他把当红小生当街坊处

跟流量明星比,刘欢在天津的“排场”实在太小了。上回他来天津参加音乐节,没走贵宾通道,跟着几个年轻乐迷挤在地铁里。有认出他的小姑娘激动得说不出话,他反倒拍拍姑娘的肩膀:“别紧张,你戴着耳机听我歌呢?我那首好汉歌前奏,是不是像咱们海河的浪?一浪赶着一浪?”
后来这事儿传开了,天津本地媒体开玩笑说“刘欢是咱们的‘地铁代言人’”。其实哪是什么“代言”,是他打心眼里把自己当天津人。他知道滨江道哪家的煎饼果子里加辣酱最香,了解海河边哪棵树下的风夏夜最凉快,甚至能和小区门口的保安大爷聊上半小时“今晚天津队踢得咋样”。
2019年,钢琴家郎朗来天津开音乐会,刘欢特意当“地陪”。没去什么高档餐厅,拉着他去南市食品街吃“狗不理包子”(虽然郎朗说“更喜欢素包”),又带古文化街淘了个泥人张的“武二郎郎朗”。“郎朗那时候总说‘欢哥,咱俩好得像亲兄弟’,我告诉他:‘在天津,咱俩是街坊——你比我小十岁,你得叫我欢哥,这规矩不能改!’”这种没架子的“天津式待客”,让不少国际友人都感叹:“原来刘欢这么接地气?”
“天津给我的是底气,我能给的只有歌声”
去年冬天,刘欢在天津做歌手的节目录制,中间休息时,他央求节目组:“让我去趟老 targeted 吧,特想喝碗老豆腐。”工作人员陪着他溜达到南马路,老摊主一看是他:“哟,欢子!今儿豆腐熬得烂,给你多加卤!”他坐在马扎上,呼噜呼噜喝完豆腐,抹抹嘴:“还是这个味儿,暖和。”
就是这么一碗老豆腐,让他说出了心里话:“我总跟人说,天津是我的‘精神老家’。这里的街坊不问你有几套房,就问‘今儿吃包子了吗’;这里的曲艺不讲究炫技,就讲究‘你说我笑,才是好汉’。这种踏实,能让人心里不慌。我在国外演出,唱到弯弯的月亮那句‘遥远的夜空,有一个弯弯的月亮’,就会想起海河的月亮——比国外的圆,因为天津的月亮,看的人心里热乎。”
所以你看,刘欢为啥总往天津跑?不是为了“回归故乡”的流量,不是为了“回馈家乡”的人设,是这座城市给了他最宝贵的东西:让他知道,再大的腕儿,也是爱吃煎饼果子、爱和街坊下棋的普通人;再高的艺术,也脱不开市井烟火的“真”。
下次在天津街头看见刘欢,别大喊“刘欢老师”,学学天津大爷,大声招呼一句:“欢哥,今儿下棋去?”他准保回头一笑,露出标志性的小虎牙:“成啊,今儿让你两步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