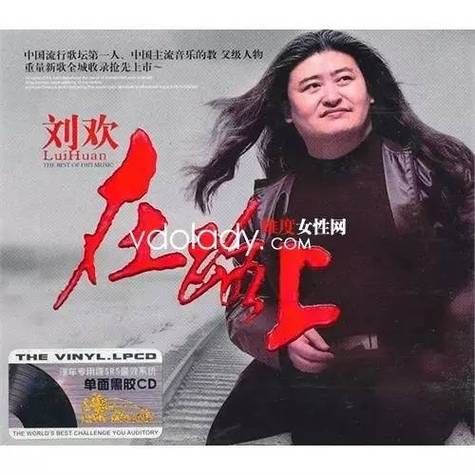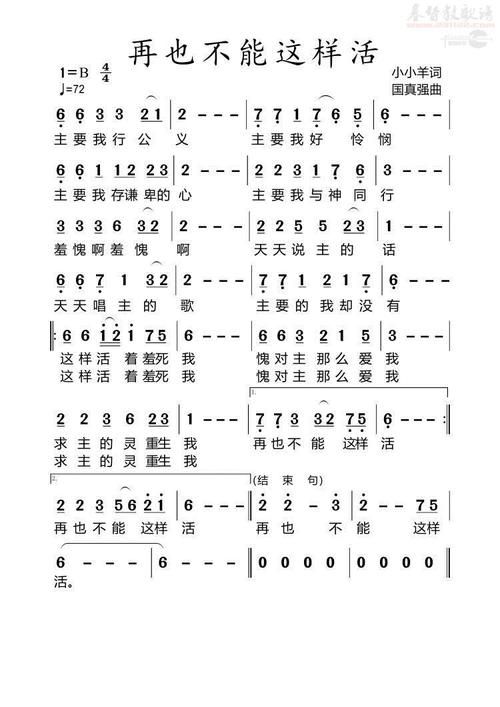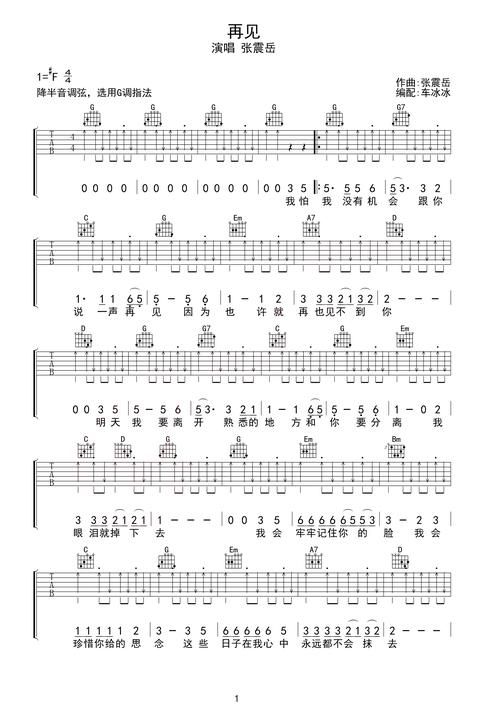清晨五点半,偃师区府店镇的一缕还没散尽的薄雾,正贴着麦田往村头飘。刘欢欢踩着露水往工作室走,裤脚沾着泥,手里攥着个刚揉好的陶坯——是个歪歪扭扭的狮子头,鬃毛捏得倒挺精神,就是鼻子有点歪。“没事,上窑烧一烧,釉一流,歪的也成特色了。”她咧嘴笑,露出的虎牙和手里这个“不完美”的狮子头,莫名地搭。

这个88年出生的偃师姑娘,如今在村里有个外号:“会捏泥巴的欢欢姐”。可在十年前,村里人提起她,多是摇头:“欢欢啊,心野得很,放着城里工作不要,非要回来跟泥巴较劲。”那会儿的她,刚从郑州一所高校的设计专业毕业,在一家装修公司做绘图员,月薪八千,朝九晚五,办公室对着落地窗,能看到写字楼外穿梭的车流。可每次视频电话,父亲总在镜头外叹气:“咱家捏了一辈子唐三彩,到你这儿,就要断了根了?”
“那些‘土掉渣’的老手艺,到底藏着什么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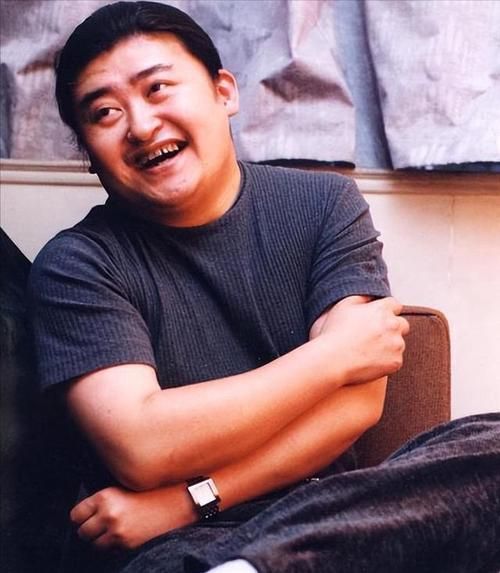
刘欢欢第一次对“泥巴”上心,是小时候趴在父亲的工作台边看。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唐三彩艺人,总爱在泥坯上刻牡丹、缠蔓草,手一捏一拉,马腿就立了起来,鸟翅膀就展开了。“那会儿觉得土,”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嫌弃,“同学家孩子都玩芭比娃娃,我手里攥着个没烧好的小马,釉料还没挂匀,蹭一手黄。”
可那些“土”东西,偏偏在她心里扎了根。2013年,父亲在窑边摔了一跤,再也弯不下腰捏泥坯。工作室的订单本上,客户名字越来越少——年轻人都往外走,谁还买这些“又沉又笨”的摆件?父亲看着积满灰的工作台,愁得饭都吃不下。“欢欢,要不……把工作室关了吧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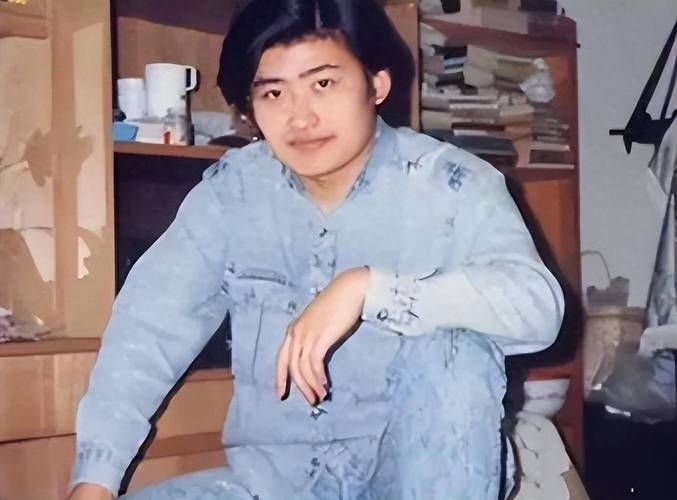
那天晚上,刘欢欢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,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她想大学时选修的“非遗设计”课,老师说:“老手艺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得活在生活中,才有温度。”她忽然爬起来,买了一张回偃师的高铁票。
父亲见到她时,眼睛亮了一下,又黯淡下去:“你回来干啥?我耽误不起你。”刘欢欢没说话,蹲下身摸了摸那些干裂的泥料:“爸,我想试试,给唐三彩‘穿件新衣服’。”
“别人说这是‘瞎折腾’,可你不去试,怎么知道不行?”
第一次“折腾”,是做唐三彩的杯子。父亲直摇头:“谁买杯子用陶的?又重又易碎!”她偏要做:把传统的马球纹改成简线条的云朵,杯柄做成牡丹花的苞,釉料不用老一套的黄绿白,试试淡淡的“天青色”——那是宋代汝窑的颜色,父亲说“唐三彩哪有用这个的,不伦不类!”
第一批杯子烧出来,果然卖不动。她扛着几个样品跑到洛阳的文创集市,被摊主怼到角落:“姑娘,你这定价还不如我塑料杯便宜,谁买啊?”那天晚上,她坐在工作室门口掉眼泪,手里的杯子被捏得微微发烫。
父亲默默递来一杯热茶:“你啊,性子太急。唐三彩从选土到烧成,要七十二道工序,哪能一步登天?”他拿起一个杯子,用手指轻轻敲了敲,“听这声音,‘叮’的是实心,‘咚’的是空心,你要听的是‘实音’。”
她忽然懂了:传承不是守着老样子不变,而是像老窑里的火,得一直烧着,才能让新东西生出来。
她开始沉下心:跟老匠人学“看土”——哪种粘土捏出来有筋骨,哪种高岭土烧出来釉面润;跟窑工学“控火”——哪段温度该升,哪段得停,窑门缝里飘出的烟颜色变了,就知道釉料熔得怎么样。她甚至跑到景德镇学现代陶艺,把那里“拉坯利坯”的技巧带回偃师,教村里的老艺人:“咱不能光靠‘捏’,机器也能帮咱把手艺做得更匀称。”
转折发生在2020年疫情期间。她拍了段制作唐三彩小视频:手从泥团里“长”出个兔子,耳朵一捏一翘,眼睛用黑釉点出,萌得不行。没想到视频火了,“这兔子能摸吗?”“我要一个!”私信像雪花一样飞来。她赶紧开通网店,把那些“不伦不类”的杯子、兔子摆件、甚至印着唐三彩纹样的手机壳挂了上去。没想到,一个月就卖了三万多。
“能让更多年轻人觉得‘这玩意儿和我有关’,就是我做的事”
现在的刘欢欢,工作室里多了二十多个年轻人,都是“95后”“00后”。有个叫小雅的姑娘,大学学的是电商,原先在深圳做直播,现在回乡帮她拍短视频:“以前看唐三彩,觉得是爷爷才喜欢的东西,现在才发现,原来兔子能这么Q,杯子能这么好看。”
她还在镇中心小学开了“陶艺课”:孩子们用泥巴捏自己的动漫偶像,捏校门口的大槐树,捏爸爸妈妈的手。有个小男孩捏了头“愤怒的小鸟”,非要给刘欢欢:“欢欢老师,这是用咱偃师的泥捏的,比你那个‘狮子头’帅多了!”她摸着孩子头上沾的泥,笑出了眼泪。
上个月,她的“唐三彩文创盲盒”上线,里面是12款 mini摆件,有骑骆驼的胡人、弹琵琶的乐伎,还有个憨憨的“胖陶俑”。原以为年轻人会喜欢“萌”款,没想到卖得最好的,是那个“胖陶俑”——有买家留言:“捏得像我爷爷,肚腩圆圆的,笑起来眼睛一条缝,看着就亲切。”
前几天,父亲看着堆满快递的工作室,对她说:“欢欢,爸以前错了,这手艺,在你手里,比在我手里活得还精神。”刘欢欢正帮一个客户给陶坯刻字,刻的是“岁月如瓷”,她笑着说:“爸,哪有什么岁月如瓷啊,不过是咱们捏泥巴的手,一直没停过。”
窗外的阳光正好,照在那些刚出窑的陶坯上,釉色流转,像极了偃师这片土地上,生生不息的烟火气。
或许,所谓的“传承”,从来不是守着一方老手艺不动,而是像刘欢欢这样——带着泥土的温度,走进年轻人的心里,让那些“老东西”,也能长出“新翅膀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