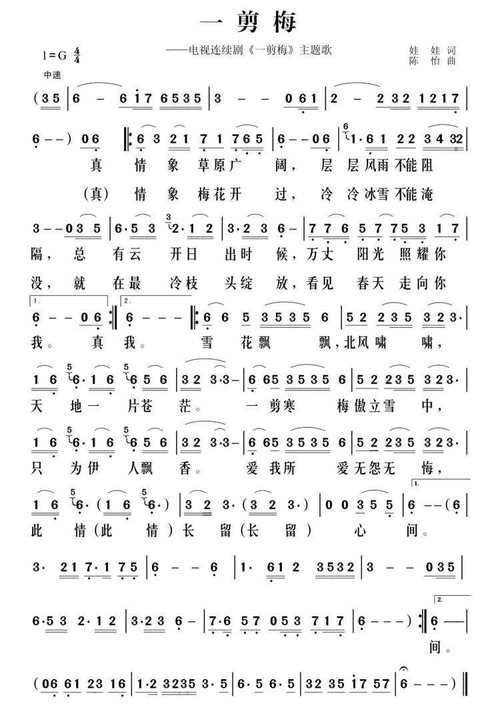早八点的阳光刚漫过中华中学的教学楼三楼,她正站在2024届(3)班的门口,手里捏着刚收上来的作文本,袖口沾了点红色的墨水——那是昨天给学生在乡土中国读后感上画五角星时蹭上的。学生远远看见她,就笑着招手:“刘欢老师,昨天您说的那个‘用短视频讲鲁迅’的点子,我们今天试拍啦!”她蹲下身,翻开作文本,指着某段旁批:“你看,你这里写‘奶奶的灶台像本旧账本’,比任何华丽的比喻都有力量,这才是你自己的声音。”
很多人第一次听到“中华中学刘欢”这个名字,都会愣一下:“是唱好汉歌那刘欢?”其实,她不是舞台上的歌手,也不是屏幕里的明星,而是南京市中华中学一位普通的“00后”语文老师,也是学生们私下喊的“欢姐”“语文界的‘人间清醒’”。从2022年站上讲台到现在,她带的班级语文平均分连续三次位列年级第一,更让无数学生说:“原来语文课可以这么‘上头’,甚至开始盼着周一。”
“我不要学生背‘标准答案’,要他们学会‘看见自己’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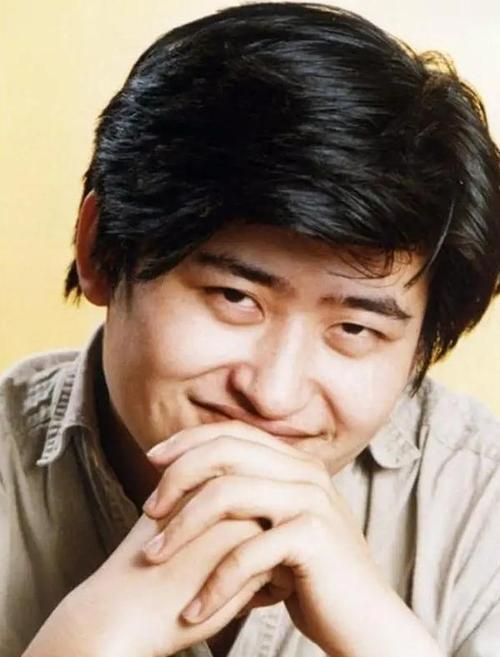
刘欢的语文课,从来不是“老师讲、学生记”的单向灌输。教项脊轩志,她不逐字逐句翻译,而是让学生分组演“归有光的日常生活”:有的组演“庭前枇杷树”,有的组演“娘亲扣我门环”,最后在黑板上画出一幅“项脊轩四季图”。“你们觉得,归有光写‘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’,为什么不说‘我想我老婆’?”她挑眉问,底下学生叽叽喳喳:“因为含蓄!”“因为枇杷树长着长着,就像老婆一直在身边啊!”她笑着点头:“对,文学的美,就是把说不出的心思,变成能看见的画面。”
更让学生“没想到”的是她的作业。写我的家乡,别人可能写“小桥流水”,她却有个“非主流要求”:“必须拍一段30秒的‘家乡声音’视频。”有学生录了菜市场的吆喝声,配文“奶奶每次买菜都要和卖豆腐的阿姨唠十分钟嗑”;有学生录了夏夜里巷口的风声,配文“爸爸摇着蒲扇,讲他小时候抓萤火虫的故事”。作业交上来,她不写“优”“良”,而是画个小小的麦克风,写:“这段吆喝里有烟火气,比任何抒情都动人。”
“欢姐总说,语文不是为了应付考试,是为了让我们学会‘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’。”高三学生小林说,“以前写作文总想着‘套模板’,现在会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,想‘如果蚂蚁会说话,它们会怎么说今天的云’?”
“当老师不是‘拯救’学生,是和他们一起‘打怪升级’”
2023年春天,班里有个叫小远的男生,数学天赋满点,语文却常年垫底,作文总是三言两语交了差。“他写假如我是苏轼,只写‘如果我像苏轼一样被贬,我就天天喝酒写诗’,”刘欢回忆,“我问他:‘你懂苏轼的苦吗?’他低头说:‘不懂,但老师说写苏轼能拿高分。’”
那天放学,她把小远留下,没聊作文,而是放了一段苏轼纪录片。“你看他被贬到黄州,连块地都得自己种,可他写出‘竹杖芒鞋轻胜马’,为什么?”小远看着屏幕里的苏轼,突然小声说:“因为他……心里有事可说?”刘欢笑了:“对啊,作文不是往模板里填肉,是你心里有什么,就说什么。你物理竞赛拿奖,说解题思路时眼睛都在发光,要能把这份‘说清楚’的劲,用写作上,肯定好。”
之后的一个月,刘欢每天午休陪小远写一段话:从“实验室里电阻冒火花”到“竞赛前手心冒汗”,从“获奖时想给妈妈打电话”到“没拿奖时躲在楼梯间哭”。三个月后,小远的作文我的“解题”与“解心”发表在校刊上,他在文末写:“以前觉得写作是件‘没劲’的事,现在发现,原来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,这么痛快。”
“‘00后’老师和学生,其实没什么代沟。”刘欢说,“我们刷一样的短视频,听一样的歌,只是我比他们多教了几年书。与其站在高处‘指点’,不如坐在他们身边,看他们怎么‘打怪’,然后递上瓶水,说‘我陪你’。”
“校园里的‘星光’,不必耀眼,但要温暖”
在中华中学,刘欢是出了名的“微信运动步数常年霸榜”。每天早上七点到校,晚上九点离开,除了上课、备课,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学生堆里:陪他们早读听背课文,午休时在办公室答疑,晚自习后和值日生一起关灯锁门。“有次我感冒了,嗓子哑得说不出话,第二早进教室,发现讲台上放着一杯胖大海和一张纸条:‘欢姐,我们今天自己背,您别说话了’,是小宇写的,他以前可是最不爱背书的。”说起这个,刘欢的眼睛弯成了月牙。
同事们说她“太拼”,家长说她“负责”,她自己却觉得“这没什么”。“当老师就像种树,你得每天看看它长得怎么样,叶子黄了要浇水,枝歪了要扶一扶。”她说,“我不求我的学生都成‘学霸’,只希望他们将来想起语文课,不是‘背不完的古诗’和‘写不完的作文’,而是‘原来我也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得这么好听’”。
前几天,毕业的学生回学校看她,带了一本自己写的书。“扉页上写着:‘感谢欢姐,让我知道,平凡的文字里,也能住着星辰大海’,”刘欢翻着书页,声音有点哽,“那一刻,突然觉得,所有熬夜备课的日子,都值了。”
其实,校园里有很多像中华中学刘欢这样的老师:他们不是明星,却用知识和爱,点亮了学生心里的光;他们没有聚光灯,却把每一堂课、每一次交流,都过成了值得珍藏的故事。或许,“星光”从不只存在于舞台和屏幕,更存在于那些俯身倾听、耐心等待、用心守护的瞬间里——就像她说的:“教育的意义,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光,然后勇敢地亮起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