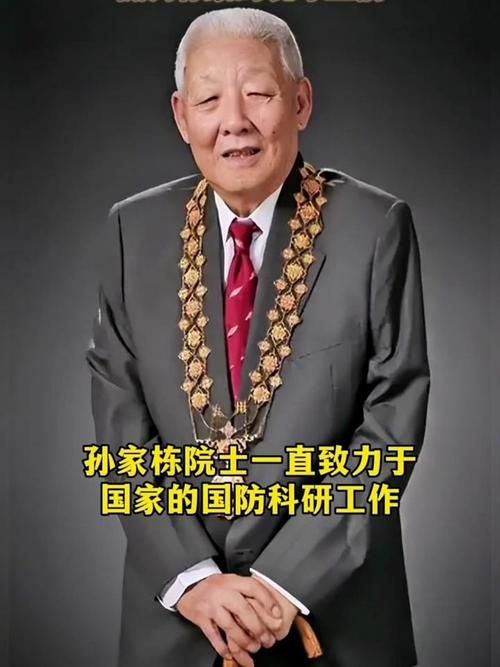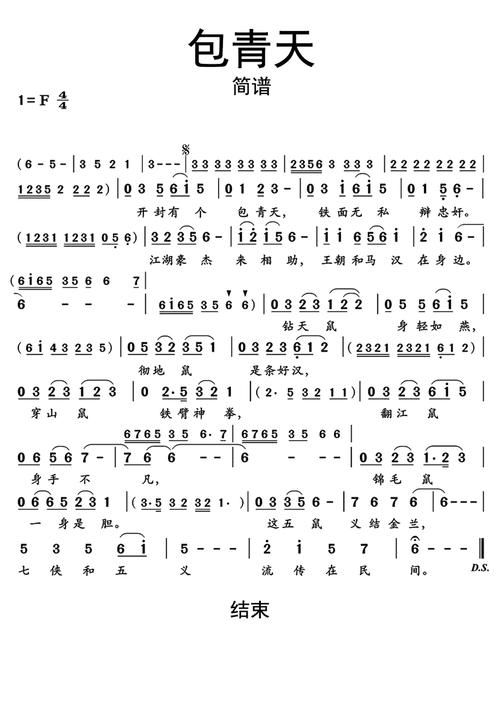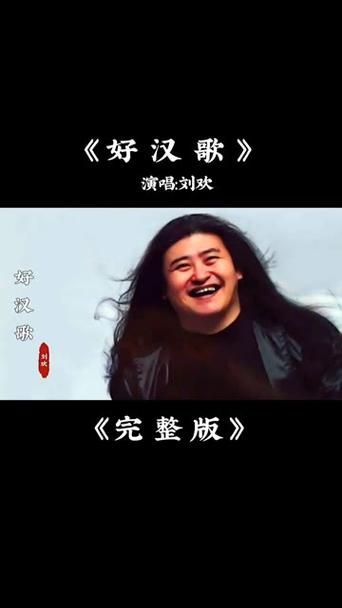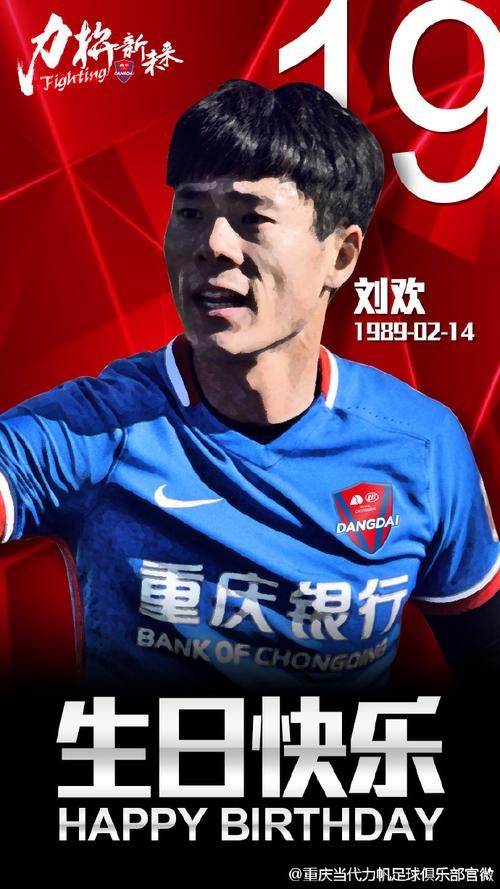聚光灯暗下去的那秒,刘欢颜手里的指挥棒还没来得及放下,观众席突然爆发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漫过舞台——不是那种礼节性的、三两秒就停的鼓掌,而是带着颤音的、此起彼伏的,连坐在第三排的头发花白的老教授都忍不住跟着节奏拍起了手。她望着台下一张张年轻的脸庞,有人眼里泛着光,有人偷偷抹了抹眼角,手里的谱子不知何时被捏出了褶皱。
这幕发生在上个月“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”的决赛现场,湖南师范大学民乐团凭借一曲茉莉花·新编拿下金奖。而站在指挥台上的刘欢颜,是个刚满20岁、扎着高马尾的大三女生,一年前还在为“能不能把古筝轮指练顺”而哭鼻子。
“我以为民乐是奶奶听的老调,直到它在我手里活了”

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刘欢颜,都会问:“你是刘欢的亲戚?”她总摆摆手笑:“不是,我爸喜欢唱好汉歌,非要给我取这个名字。”但这个名字仿佛自带“民乐buff”,她从小被家里的收音机“泡”大——奶奶房间里常放二泉映月,爸爸车里循环春江花月夜,可那时候她对这些“老古董”毫无兴趣,直到小学三年级,音乐老师说:“欢颜,你手长,试试古筝?”
初学的日子枯燥到让人想放弃。练渔舟唱晚时,小指勾弦的力度总不够,老师敲着谱子说:“听这声音,像没煮熟的米粒!”她躲在琴房哭,眼泪滴在琴码上,把弦都洇湿了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当她拨动琴弦,听清了低音区像溪水流淌,高音区像鸟儿扑棱,那段旋律突然让她想起小时候和奶奶在乡下看萤火虫的夏夜——原来民乐不是课本里干巴巴的文字,是能装着整个人间情味的。
考入湖南师大后,她抱着古筝加入民乐团,才真正打开了新世界。这里没有“独奏家”,只有“你弹错了,我跟着你改”的默契;唢呐的嘹亮能盖过古筝的清越,二胡的呜咽又能和笛子的悠扬缠绵。她第一次和乐团合奏高山流水,当古筝的泛音、古琴的走手音、琵琶的轮指交织在一起,她忽然懂了什么叫“知音”——不是某一个人的光芒,是每个人手里的乐器,都成了别人耳朵里的风景。
“学生乐团?我们偏要和‘专业’掰掰手腕”
湖南师大民乐团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,像个藏在岳麓山脚下的“宝藏”。没有华丽的排练厅,琴房还是上个世纪的水泥地;没有高额经费,乐器大多是师兄师姐“传”下来的——那台用了20年的古筝,琴边还留着前任主刻的“2008,加油”。但就是这群“草根”学生,偏要和“专业”掰手腕。
去年备赛茉莉花·新编,导演组泼了冷水:“传统民乐改编不好弄,弄巧成拙就成‘四不像’。”刘欢颜不服气:她去音乐系图书馆翻资料,找到民国时期茉莉花的工尺谱;跑到湘剧团请教老艺人,学湖南花鼓戏里的“滑音”技巧;甚至拉着学计算机的同学编程序,把古筝的音色和电子乐的鼓点混音——有人笑她:“不伦不类!”她却说:“民乐活着,就不能只躺在博物馆里。”
最难的合排,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。封校期间,30多个人挤在小小的排练厅,隔着一米距离练习。吹笛子的男生戴着口罩,气息总不稳;拉二胡的女生怕传染人,自己在家对着视频练,手指磨出了茧子。刘欢-颜每天早上7点起床,把大家的练习视频剪成合集,逐帧指出问题:“这里你快了半拍”“那个颤音要再柔一点”。有次她熬夜改谱,趴在桌子上睡着,手里还攥着笔,谱子上晕开了一大片墨渍。
决赛那天,当茉莉花·新编的第一个音符响起,没人想到这首“老歌”能这么“燃”。古筝的轮指像雨打芭蕉,唢呐的高亢像冲破云层的霞光,中间突然插入一段爵士鼓的节奏——台下一个评委猛地坐直了身子,眼睛瞪得圆圆的;另一个评委悄悄对旁边人说:“这学生团的编曲,比专业院团还敢想!”
“我们不是在‘复兴’民乐,是在让它‘回家’”
领奖那天,有个老评委拉着刘欢颜的手说:“你们让民乐有了‘烟火气’。”她想了想,觉得“烟火气”这个词特别贴——民乐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“雅乐”,是街头巷尾的唢呐响是红白喜事的锣鼓声,是奶奶哼着哄你睡觉的小调。
现在的民乐团,成了湖师大最“出圈”的社团。他们把孤勇者改编成民乐版,在短视频平台火了,评论区里00后留言:“原来唢呐也能这么‘燃’!”他们走进中小学,教小朋友用竹笛吹孤勇者,有家长说:“孩子以前只爱听流行歌,现在吵着要学古筝。”
刘欢颜说,自己不是什么“民乐传承者”,只是个“愿意把好东西分享给同龄人”的普通学生。就像她指挥时总说的:“民乐不是文物,是活的。它会老,但不会死,因为我们年轻人,还在给它添新故事。”
台下的掌声还在继续,刘欢颜看着乐团的伙伴们——那个总把唢呐擦得锃亮的男生,那个笑起来眼睛像月牙的女生,他们手里抱着乐器,像抱着自己最珍贵的秘密。她忽然明白,所谓“传承”,或许不是守住过去,而是让过去的旋律,能在今天的年轻人的心里,活成新的模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