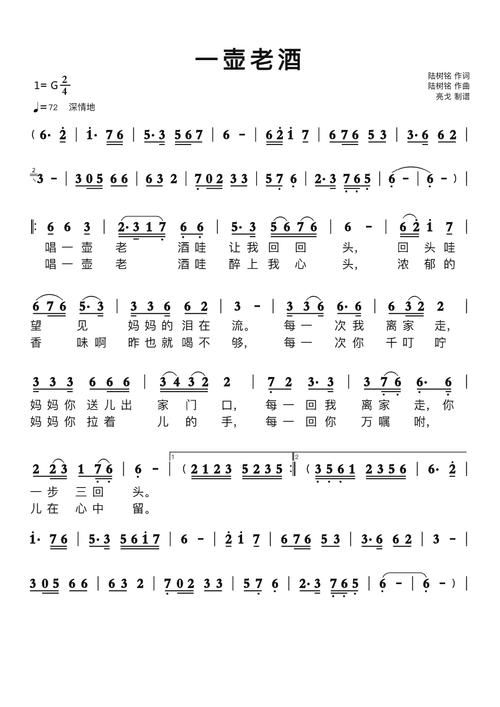2011年甄嬛传开播时,没人能想到这部宫斗剧会成为“永不下架的国民剧”。直到今天,还有人会在深夜反复刷“嬛嬛一.xml001”,跟着眉卿念“菀菀类卿”,甚至为“安小鸟”的黑化又怒又怜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,让这些情节“长在观众DNA里”的,除了演员的演技,还有刘欢藏在旋律里的“宫心计”。

刘欢接下甄嬛传时,根本没想“写歌”,他想“写命”
2010年,导演郑晓龙找上门时,刘欢正在筹备个人演唱会。作为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的“御用作曲人”,他早已经是华语音乐圈的“定海神针”——但一听要做甄嬛传的音乐,他却犹豫了。“这剧里没英雄,都是活生生的人,被命运推着走的人。”刘欢后来在采访里说,“写悲壮容易,写这种‘在夹缝里找光’,难。”

难在哪儿?难在不能“端着”。宫斗剧的配乐,要么浮夸得像京剧锣鼓,要么缠绵得像琼瑶剧,但刘欢要的是“让观众忘记这是配乐”——就像空气,你平时注意不到,可少了它,人物就喘不上气。于是他推掉了所有工作,啃完了原著,又跟着剧组拍了三个月,连宫女的走路姿势、太医的把脉节奏都记了下来。“我得知道,甄嬛在承恩时心里是冷的,华妃在罚跪时眼里是热的,这些情绪怎么变成音符?”
菩萨蛮不是片头曲,是“甄嬛的日记”
很多人以为甄嬛传的片头曲是菩萨蛮,其实这首歌是“总主题”:它不是唱某个人的命运,而是唱整个后宫的“局”。“小山重叠金明灭,鬓云欲度香腮雪”,琴声一起,镜头从故宫的红墙扫到窗外的牡丹,像一只无形的手,把观众按进了“一入宫门深似海”的漩涡。
刘欢写这首歌时,拒绝了古筝、琵琶这些“标配乐器”。他找来古琴家成公亮,用那张被磨得发亮的宋代古琴,弹出了“鬓云欲度”的慵懒,“懒起画蛾眉”的倦怠——不是闺怨,是一种“知道宿命却无力反抗”的空。“你看甄嬛刚入宫时,弹琴是不是总走弦?那不是技不如人,是她心里还装着‘愿得一心人’的傻。”刘欢说,“琴弦震久了会松,人心也是。”
凤凰于飞也不是“情歌”,是“甄嬛的自我了断”
如果说菩萨蛮是后宫的“全景图”,那凤凰于飞就是甄嬛的“内心独白”。“旧梦依稀,往事迷离,春花秋月里”,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,觉得是后宫爱情的挽歌,直到看到63集甄嬛回宫的戏——她穿一石青色旗装,站在碎玉轩的梨树下,对着皇上行礼时,手指在袖子里攥得发白。
这时你再听“从今后,缠绵纠结,两情悦,愿如凤凰于飞,恩爱不绝”,会发现根本不是“甜”。刘欢在编曲时,故意让女声的拖沓感比男声重半拍,像一个人的脚步追着另一个人跑,却总差一点。“凤凰于飞,不是比翼双飞,是‘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’后的‘云胡不悲’。”刘欢解释,“甄嬛唱这首歌时,心里早就没了果郡王,她只是在和自己告别。”
很少有人知道,凤凰于飞的歌词里藏了个“彩蛋”:“得非所愿,愿非所得,看命运嘲弄,造化游戏”。这14个字,其实是全剧的核心——甄嬛想要的“一生一世一双人”,命运偏给她“一入宫门深似海”;她想要的“单纯美好”,却逼她学会“笑里藏刀”。刘欢用旋律把这种“错位”做到了极致:副歌部分明明是激昂的,听起来却像在哭。
没人比刘欢更懂“宫斗”:音乐里的“人设密码”
除了主题曲,刘欢还为每个主要角色写了“专属旋律”。华妃的戏码一响,弦乐就带点铜管的尖锐,像她额头的“牡丹花”一样扎人;安陵容每次下毒前,琵琶都会弹个不和谐的滑音,像她心里憋着的那口“恶气”;就连温实初这个角色,用的都是古琴的泛音,清冷得像他永远“把爱意藏在医术里”的执拗。
最绝的是“沈眉庄”的配乐。她被贬为“答应”时,刘欢没用大提琴的低沉,而是让长笛吹出断断续续的调子,像她在冷宫里抱着胧月说的“娘娘别怕,有眉娘在”。后来她难产而亡,那段“凋零”的旋律,其实是把她在开头的“甜笑”主题,故意弹慢了三倍——不是哭,是“笑不出来”的空。
“观众可能不知道,这些旋律里藏着‘性格伏笔’。”刘欢说,“就像甄嬛刚入宫时,她的主题里还有点童谣感,可到了斗赢皇后,那旋律就变成了‘一串一串的碎音符’,像把真心都揉碎了,包上坚硬的壳。”
12年过去,我们为什么还在听刘欢的甄嬛传?
前阵子看到一个网友说:“失恋时循环凤凰于飞,突然懂了甄嬛那句‘之前的眼泪是为果郡流,现在的眼泪是为我自己流’。”这或许就是刘欢音乐的魔力——他从不直接告诉你“角色有多惨”,而是把情绪揉碎了,藏在琴弦里、歌词里,让你在某个深夜突然被击中。
其实刘欢自己从没把甄嬛传的配乐当成“作品”,他说“我只是在给故事穿衣服”。但这件“衣服”,却比很多剧情本身更让人难忘。就像菩萨蛮的最后一句“相去迟尺,竟天涯”,没人说得清到底是在唱后宫的距离,还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——有些愿望,看着近,却一辈子也够不着。
下次再看甄嬛传,不妨戴上耳机,把声音调大些。或许你会发现,刘欢早就用音乐,把“红墙绿瓦里的爱恨嗔痴”,变成了一首值得用一生去品的老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