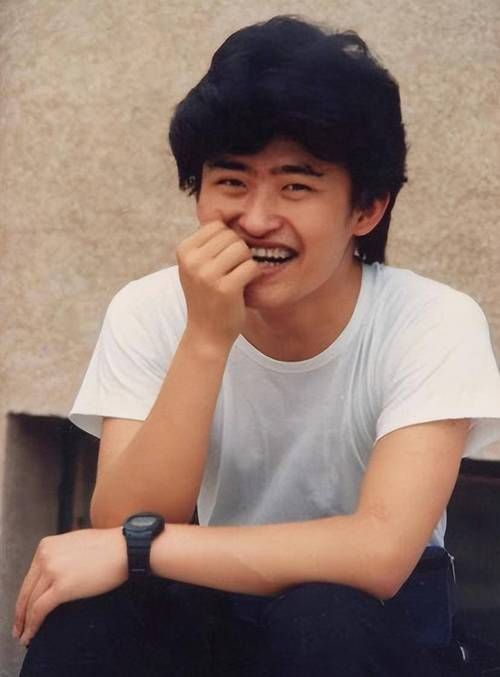2023年九月末的北京,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,一束追光打在刘欢身上。他穿着深灰色中式立领衫,手指在钢琴琴键上轻轻掠过,身后杭盖乐队的成员们已调试好马头琴、图瓦喉鸣和电吉他。当第一个音符从刘欢的唇间与指尖同时流淌出来时,台下的观众突然集体安静了——那首三十年前的不能这样活,在马头琴苍凉的滑音和电吉他失真的riff里,竟像被注入了新的血液。有人小声惊呼:“这是刘欢?还是杭盖?”

更让人意外的是,这场演出的主题叫“轮回”。刘欢在采访里说:“我听杭盖的歌,像看到小时候在内蒙古草原上看到的河流,表面上还是那条河,水却一直在往前流。”而杭盖乐队的主唱义拉拉塔则挠着头笑:“刘欢老师总说我们的音乐有‘根’,其实我们才是从他那一代人的歌里,找到了怎么让‘根’活过来的方法。”
刘欢的“轮回”:从流行巅峰到民族深处的跋涉

很多人对刘欢的印象,还停留在好汉歌里“大河向东流”的豪迈,或是弯弯的月亮里温润如玉的吟唱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,这位中国流行音乐的“活化石”,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了自己的“轮回”。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刘欢与莎拉·布莱曼演唱的我和你,用极简的旋律唱出了全人类的共鸣。那之后,他突然淡出大众视野,一头扎进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海洋。“我总在想,流行音乐能红多久?那些没被记录下来的山歌、长调,会不会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消失?”刘欢曾在一次音乐座谈会上坦言,自己花了五年时间,带着录音设备跑遍了云南、青海、内蒙古,收集了上千小时的一手音频。
在云南怒江大峡谷,他为了记录傈僳族“摆时”调,在老乡家借住了半个月,每天跟着老人们上山砍柴,下山时学他们用“木叶吹调”;在青海玉树,他喝着酥油茶,跟着格萨尔王史诗的说唱艺人,记下了长达二十小时的唱段;最让他难忘的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,一位80岁的蒙古族老阿妈,用带沙哑的嗓音给他唱鸿嘎鲁(天鹅),唱着唱着就哭了:“我阿妈教我唱的时候,草原上还有那么多天鹅,现在……现在都看不到了。”
这些经历,像一颗颗种子,在刘欢心里慢慢发芽。2016年,他推出专辑记忆,里面没有口水歌,只有经过重新编曲的民歌,比如侗族大歌蝉之歌,他用钢琴铺底,加了弦乐四重奏,却保留了侗族女人多声部和声里那种原始的生命力。当时有人批评他“不务正业”,他却在节目里说:“音乐不是用来固化的,是用来呼吸的。你把它放在不同的环境里,它才能活下来。”
杭盖的“轮回”:从草原酒吧到世界舞台的野蛮生长
如果说刘欢的“轮回”是主动的回归,那杭盖乐队的“轮回”,则更像一场意外的“出走”。
成立于2004年的杭盖,最初只是五个来自内蒙古的年轻人,在北京后海的酒吧里翻唱民歌、摇滚乐。他们没有想过要做世界音乐,只是想“用自己喜欢的乐器,唱自己的生活”。主唱义拉拉塔说:“刚来北京时,我们穿着蒙古袍上台,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,说我们是‘行为艺术’。”但他们坚持用马头琴、雅托噶(蒙古筝)、火不思这些传统乐器,甚至把牧民家里的羊皮袄、马鞍都搬上了舞台。
转机出现在2010年。杭盖去比利时参加一个音乐节,原以为没人会听他们的“草原摇滚”,没想到台下外国观众跟着节奏疯狂甩头,演出结束后,唱片公司的排队能绕场三圈。“我们突然发现,那些我们认为‘土’的东西,在外国人眼里是‘酷’的。”吉他手手登扎布说。
从那以后,杭盖开始了“野蛮生长”。他们把民歌希格希日改编成重金属版,马头琴的滑音配合电吉他的扫弦,像草原上的一场暴风雨;他们把图瓦喉鸣呼麦与布鲁斯即兴融合,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出时,美国乐迷惊叹:“这声音像来自外星球,又像来自大地深处。”
杭盖的“轮回”,是带着草原的音乐基因,闯进了世界音乐的洪流。他们没有刻意迎合谁,只是把牧民喝酒时的歌、摔跤时的呐喊、赛马时的号子,用现代音乐的结构重新包裹。义拉拉塔说:“我们唱的从来不是‘复古’,是‘现在’。草原上的人现在也开摩托车、用手机,他们的声音,本来就应该活在今天。”
当“教父”遇上“摇滚魂”:两个“轮回”的奇妙共振
刘欢第一次听到杭盖的音乐,是在2015年的一个音乐颁奖后台。当时杭盖正在后台准备上台,音响里突然传来他们的花,马头琴的旋律像一阵风,吹得刘欢停下了脚步。“我当时就愣住了,”刘欢后来回忆,“这音乐里有我找的那种‘呼吸感’——既有传统的东西,又活生生地往前走。”
真正让两人走到一起的,是2020年疫情期间的一场线上演出。当时刘欢被隔离在家,杭盖在内蒙古,两人隔着屏幕合唱了一首鸿雁。刘欢用钢琴弹出旋律,杭盖的马头琴跟上,义拉拉塔的嗓子一起,突然两个人都哭了。“那一刻没有老师也没有乐队,只有两个音乐人,在对一首共同的歌说话。”刘欢说。
2023年的“轮回”演唱会,就是这场线上演出的实体版。舞台上,刘欢不再高高在上,而是和杭盖的成员们围坐一圈,像草原上的“乌查”(蒙古语:朋友)一样聊天、唱歌。唱天堂时,刘欢让手登扎布用火不思solo,自己退到后面微笑;唱不能这样活时,义拉拉塔把话筒递给刘欢,自己拿起马头琴跟着拉台下的观众,有人跟着唱,有人跳起了蒙古舞,分不清谁是演员,谁是观众。
“刘欢老师让我们知道,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”手登扎布说,“而杭盖让刘欢老师看到,年轻一代怎么让传统像草原上的草一样,年年发芽。”这或许就是“轮回”真正的意义——不是简单的重复,而是像河流一样,在流淌中不断遇见新的支流,最终汇成更广阔的海洋。
音乐的“轮回”,从来不是回到过去,而是带着记忆走向未来
演出结束时,刘欢和杭盖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台上,鞠躬。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,有人喊“再来一首”,有人喊“你们才是中国音乐的希望”。刘欢拿起话筒,笑着说:“其实我们不是什么‘教父’,也不是什么‘摇滚魂’,我们都是音乐的搬运工,把老祖宗留下的声音,搬给今天的人听。”
杭盖的义拉拉塔则用蒙古语说了一段话,翻译过来是:“我们的音乐,就像牧民家的羊,生了一代又一代,毛还是那毛,但羊永远在跑。”
走出国家大剧院时,秋风吹过长安街,路边的银杏叶开始泛黄。突然想起刘欢在采访里说的一句话:“音乐这东西,你越想抓住它,它就越像沙子;你松开手,它自己就会聚成河。”或许,“轮回”从来不是让我们回到过去,而是让我们带着过去的记忆,勇敢地走向未来。就像刘欢和杭盖,一个从流行巅峰走回民族深处,一个从草原小径走向世界舞台,他们用音乐告诉我们:所有伟大的生命,都在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轮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