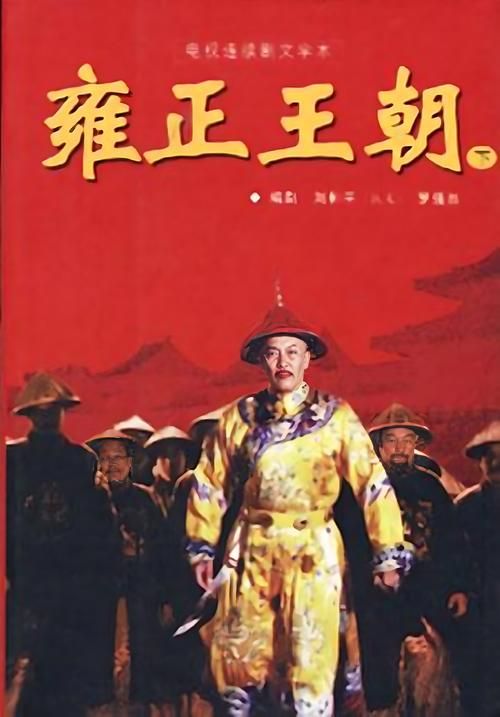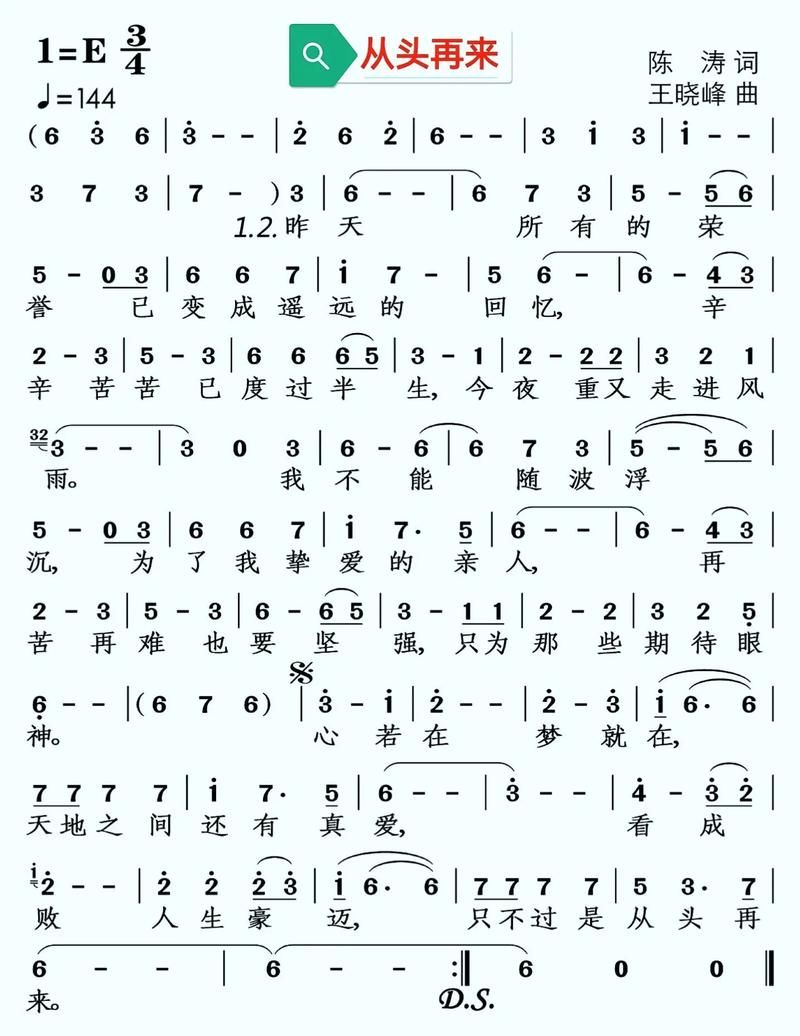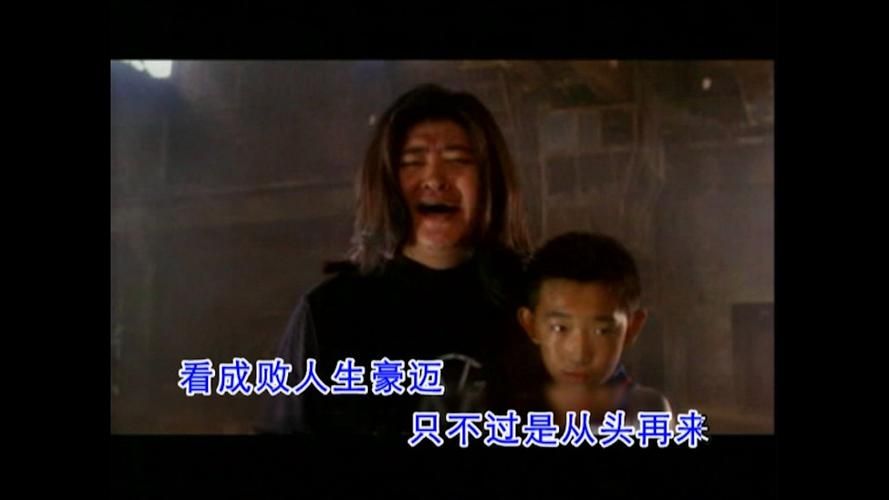你还记得1990年的春晚吗?电视机还是显像管的,天线要用手“掰”出雪花,我妈总说“离远点看对眼睛好”,但那天全家人都挤在沙发前,盯着屏幕里两个唱歌的人——韦唯穿一身红,像团火;刘欢一身黑,像座山。前奏一起,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头!”我爸手里的茶杯顿在半空,我妈跟着晃脑袋,连我蹲在地上玩积木的小手,都忘了动。

那年北京亚运会,是“中国想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名片”。主题曲选来选去,落在了徐沛东和张藬肩上。徐沛东后来回忆:“要写亚洲的歌,得有山的厚重,也得有河的奔涌。”找谁唱呢?想来想去,乐坛里能把“厚重”和“奔涌”唱出魂的,只有韦唯和刘欢了——一个高亢得能顶破屋顶,一个深沉得能沉进心底,两人站一起,活脱脱是“亚洲的骨架与血脉”。
录这首歌时,韦唯刚从欧洲回来,抱着吉他在 studio 练了半个月。她总说:“这首歌得唱出‘我们’的气势,不是‘我’的。”为了那句“河像热血流”,她喝了半锅冰糖雪梨,嗓子唱到冒烟,还攥着徐沛东的手问:“老师,你说热血够不够烫?”刘欢呢,非要找到“站在黄河边上吼”的感觉,录音室的工作人员说:“他攥着拳头,胳膊上的青筋都爆了,好像面前真有万马奔腾。”最后混音时,两人的和声叠在一起,工程师猛地拍了下大腿:“这哪是唱歌?是把亚洲的骨头都唱响了!”

亚运会开幕式那天,9万人的工人体育场,骤然安静下来。韦唯的声音像把剑,劈开暮色,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头!”9万人的声音突然跟着炸开——“河像热血流!”刘欢接上那句“我们亚洲,云也手握手”,整个体育场的人都在挥舞着手臂,灯光汇成一片星海。后来刘欢在采访里红了眼眶:“那会儿我懂了,音乐不是个人的事,是千万人站在一起时,心里那股劲儿。”
那时候的我们,刚走出国门没几年,口袋里没多少钱,但腰杆挺得直。村里卖货的拖拉机上,放的是亚洲雄风;工厂午休时的录音机,循环的是“我们亚洲,树都手拉手”。我爸说,有次他骑车去邻县送货,下坡时放了这首歌,他跟着踩脚蹬,骑出了飞起来的感觉——不是车快,是心里有股火在烧。
现在回头看,亚洲雄风一点都不“土”。没有华丽的转音,没有噱头,就靠最简单的旋律,配上两个嗓子里的“真”。韦唯的声音是“山”,带着不屈的棱角;刘欢的声音是“河”,藏着包容的力量。合唱时,没有谁抢谁的戏,是“山与河”的对话,是“亚洲”在开口。所以30年后,KTV里还有人抢着唱这首歌,吼到嗓子沙哑也不觉得累——唱的不是歌,是当年那个挺着胸、抬着头、敢对世界说“我们来了”的自己。
去年翻出旧相册,发现1990年的我,举着个塑料喇叭,嘴张得老大,仿佛在跟着屏幕里的韦唯刘欢一起吼。现在给我家孩子放这首歌,他眨着眼睛问:“妈妈,这个歌为什么听起来像在举重?”我没说话,只是把他抱起来,让他看窗外的万家灯火。
有些歌,从来不会老。就像30年前那晚,9万人的呐喊,刻进了一个时代的骨头里;也像现在,每次听到“我们亚洲,山是高昂的头”,心里还是会那股——热气腾腾的劲儿。
这股“雄风”,什么时候听,都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