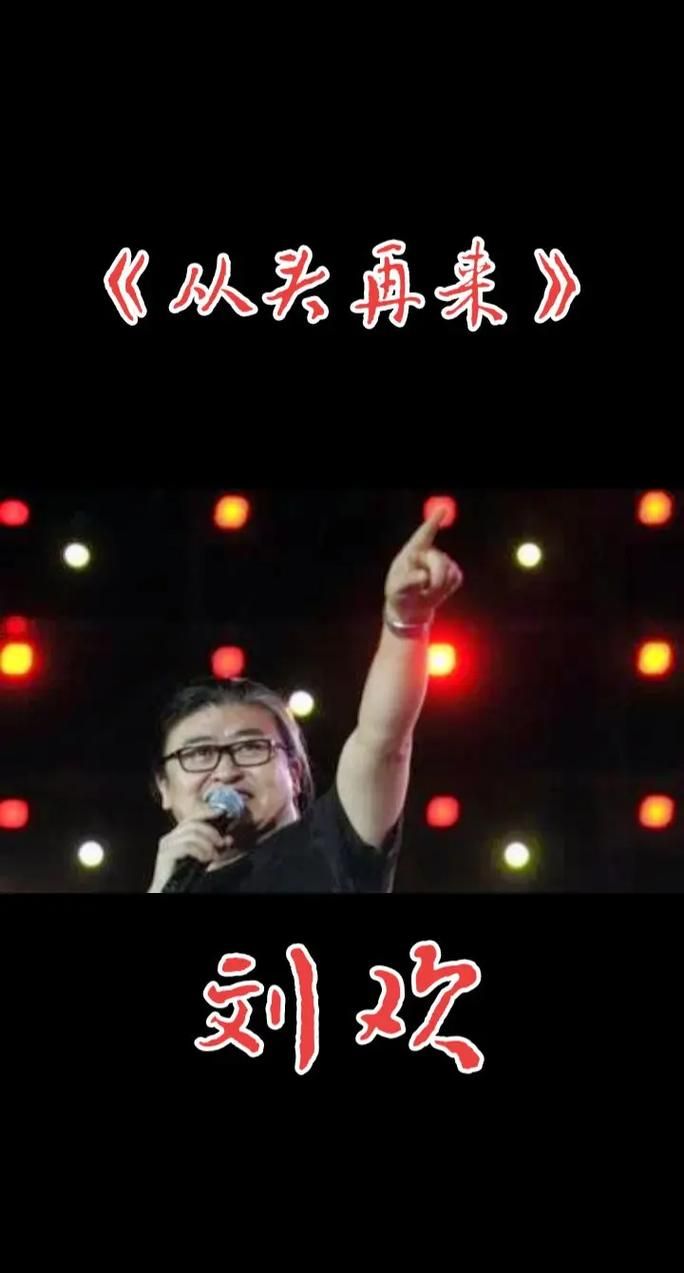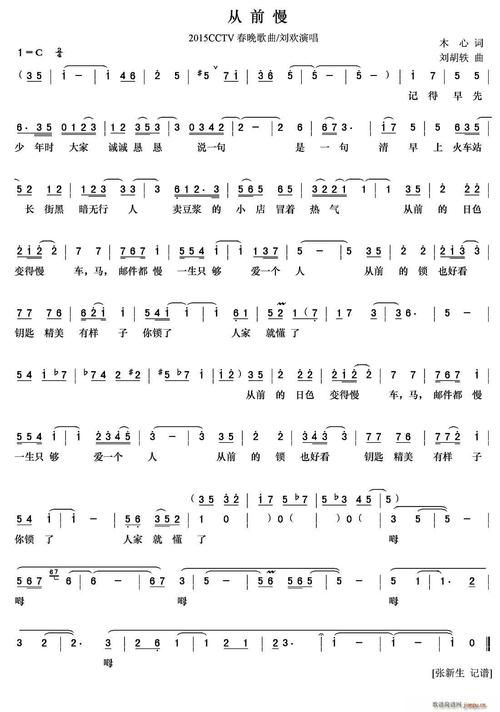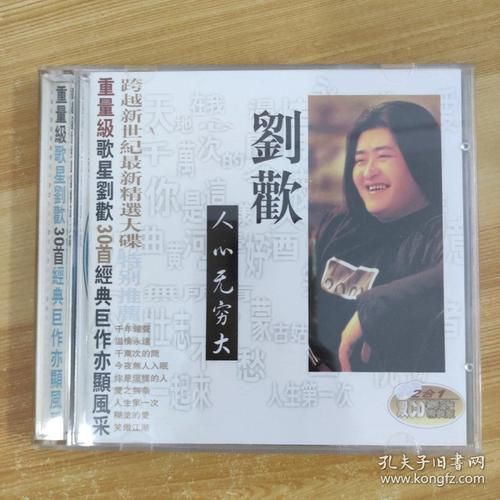在很多人眼里,老师这个职业似乎总带着点“刻板印象”——严肃、循规蹈矩,每天重复着“知识点划重点、作业批改讲评”的流程。但如果你认识中牟的初中语文老师刘欢,可能会彻底打破这种认知。她不是“网红”,也不是“教育专家”,只是一个普通的班主任,却在学生心里种下了“盼着上学”的种子,在家长口中成了“遇见了就是孩子福气”的存在。她到底做对了什么?

从“怕语文”到“盼语文”:她的课堂里有“故事会”,也有“小剧场”
第一次走进刘欢的语文课,你可能会有点“恍惚”——讲台上没有厚重的教案,只有几本翻旧了的课外书;学生不是正襟危坐,而是有的趴在桌上托着下巴,有的甚至半站着讨论,教室里不时传来一阵笑声,然后又突然安静下来,听得入神。

“语文哪有那么难背?你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,鲁迅小时候不也偷偷爬到墙上摘桑葚吗?”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,刘欢没有直接翻译课文,而是给学生讲起了自己的童年:“我小时候也有一片‘百草园’,就是村头的小河边,夏天捉蜻蜓,秋天摘野菊花,被蜜蜂蜇了也不哭——你们有没有这样的‘秘密基地’?”话音刚落,教室里炸开了锅:“老师我!我家楼下有片小树林,我藏了我的奥特曼卡片!”“老师老师,我奶奶家的菜地,我偷摘过西红柿!”
一篇枯燥的课文,在她的三言两语里,变成了“童年故事会”;学古诗时,她带着学生在教室里“演”起来:“‘举头望明月’,你们抬头看看,教室里的灯像不像月亮?”“‘低头思故乡’,如果你是李白,这时候会想家里的什么?”有个学生突然举手:“老师,我会想妈妈做的红烧肉!”全班哄堂大笑,可谁也没想到,那天放学后,那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男孩,在作文里写道:“刘欢老师的语文课,像吃红烧肉一样香。”

这样的课堂,从初一教到初三,她的学生语文平均分始终排在年级前列,但更让她骄傲的是:“以前最怕写作文的孩子,现在会主动找我:‘老师,我今天看到一个老奶奶卖菜,想写写她’。”
班主任的“硬核”柔情:学生的“烦心事”,她记得比自己的事还清楚
作为班主任,刘欢的办公桌上总有一个褪色的“小秘密本”——里面记着每个学生的“小事”:小A爱吃学校食堂的糖醋里脊,但周三没有;小B爸妈在外地打工,每周五下午放学都会去校门口的文具店待半小时;小C数学不好,总说“我可能不是学习的料”……
去年冬天,班里的“调皮鬼”小D因为跟同学打架,被叫到了办公室。刘欢没有骂他,只是递给他一杯热奶茶:“你喝口热的,跟我说说,当时是不是觉得特别委屈?”小D愣了一下,接过奶茶,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:“他们说我抄作业,其实……我只是那道题不会,想看一眼他的……”那天下午,刘欢陪小D在操场走了三圈,从“抄作业”聊到“爸爸总说他没用”,最后说:“咱们定个规矩,不会的题来问我,咱慢慢学,但打架能解决问题吗?不能,对不对?”
后来小D毕业时,在给她的小秘密本上画了一幅画:一个举着奶茶的老师,旁边歪歪扭扭写着:“刘欢,你是我见过最‘烦人’的老师,也是我最好的老师。”
这样的“烦人”,还有很多:有学生家里条件不好,她悄悄给买了套校服;有学生父母吵架闹离婚,她连续一个月每天放学陪他走一段路;有学生沉迷手机,她没有没收,而是说:“你要是能每天少玩半小时,我陪你看一部电影,好不好?”家长会上,有家长拉着她的手说:“刘老师,我家孩子回来不说学校的事了,就爱说‘我们刘欢说’……我知道,你费心了。”
“我不是名师,就是个‘陪孩子长大的普通老师’”
说到自己的“走红”(其实是家长间的口口相传),刘欢总是摆摆手:“我哪有什么秘诀?就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呗。”她的手机里存着几百学生的照片,从刚上初一的“小不点”,到毕业时的大姑娘小伙子,每个照片下都配着一行小字:“今天运动会,小E拿了800米第三名,开心到跳起来!”“小F写的诗被校刊采用了,比我还兴奋。”
有年轻老师问她:“怎么才能让学生喜欢你?”她想了想,说:“少点‘你应该’,多点‘我们一起’。比如‘你们应该好好学习’,不如说‘我们一起把这篇课文啃下来,好不好?’;‘你们不应该打架’,不如说‘咱们一起想想,除了打架,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?’教育不是‘管’,是‘陪着走’。”
现在的刘欢,依然每天早出晚归,备课、改作业、陪学生跑操、听他们说“小秘密”。有人说她太拼,她说:“你看他们从懵懂懵懂的样子,长成了有担当的小大人,这种成就感,比什么都值。”
中牟的教师很多,像刘欢这样的也很多——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,用最朴素的方式,守护着孩子的成长。或许,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:不张扬,却有力量;不刻意,却能温暖人心。
下次如果你问我:“好老师是什么样的?”我会说:“去看看中牟的刘欢老师吧,她站在那里,就像春天里的一棵树,默默为学生遮风挡雨,却又让他们总朝着光的方向生长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