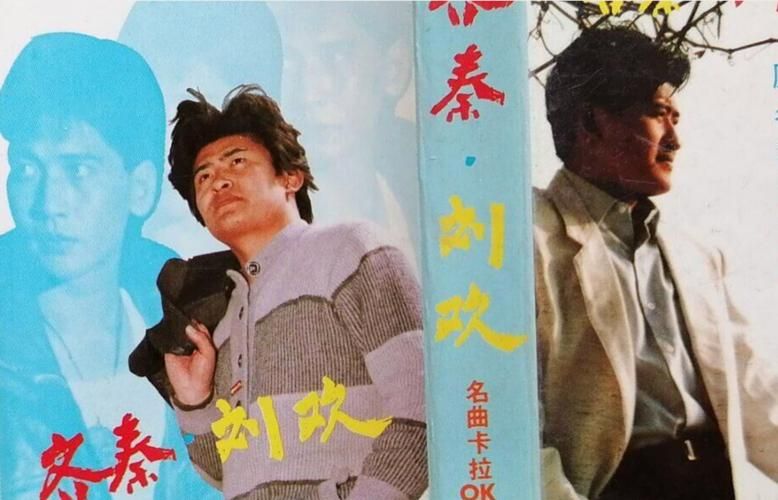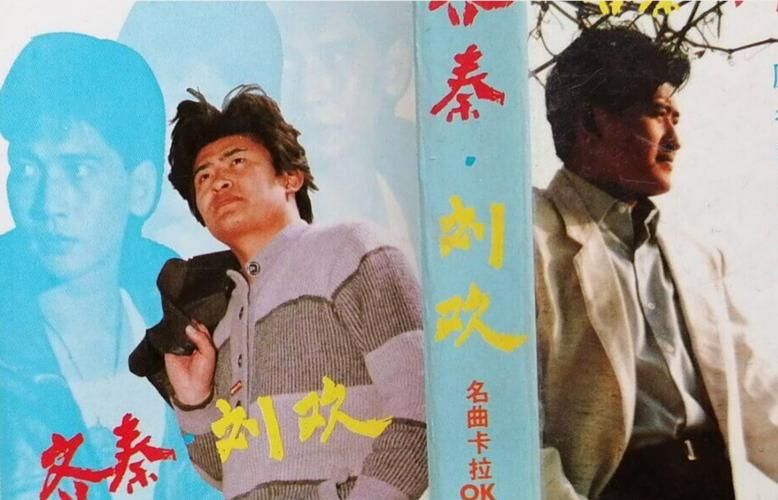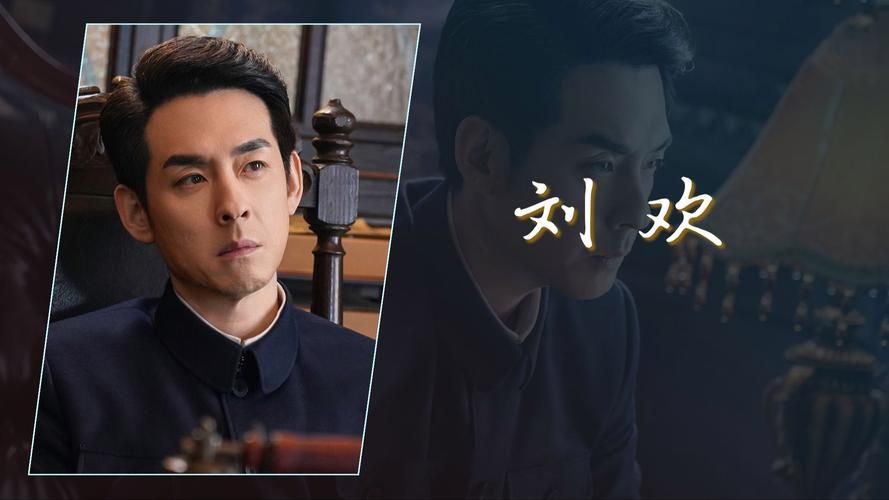秋天的衢州,桂子落满衢州学院的青石板路。早上七点,总有学生在操场边的老樟树下练声,琴声混着方言唱的黄梅调,偶尔会飘进刘欢的歌声——不是CD里的录音,是学生抱着吉他弹弯弯的月亮,跑调的副歌里藏着认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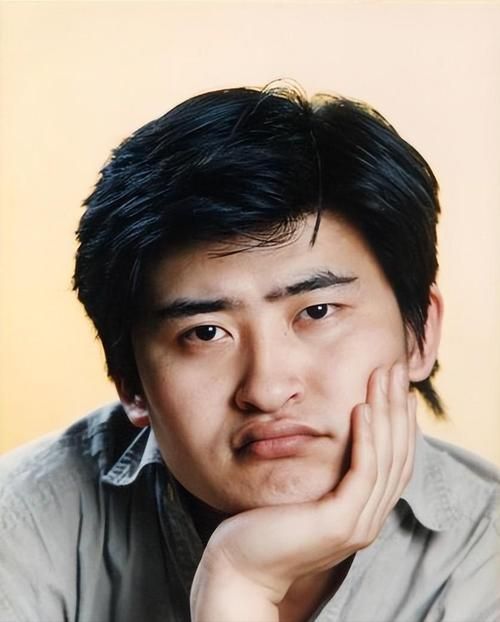
你有没有想过,那位唱了好汉歌天地在我心的刘欢,会和这座浙西小城的高校,扯上什么关系?
衢州学院:被音乐“撞了一下腰”的地方

衢州学院在衢州不算“显眼”——它不像省城高校那样站上热搜,也不像艺术名校常有明星往来。但走在校园里,你能闻到一股“混着土味的灵气”:音乐学院的学生把南孔礼乐改编成流行曲,食堂阿姨的方言说唱在网上小火过,就连校门口的煎饼摊老板,都能跟着我和你的调子颠勺。
“刘欢来过?”大四学生小雨正在排练厅练钢琴,抬头时睫毛上沾着点灰,“我们老师倒是提过,说刘欢的歌‘有地气’,像衢州的烂柯山,表面平平无奇,往里走全是故事。”
故事要从三年前说起。那届毕业晚会,音乐系老师策划了个“经典新唱”环节,挑了刘欢的千万次的问。学生们不乐意:“太老了!”直到老师放了段纪录片——刘欢在北京筒子楼里写歌,邻居在楼下炒菜,油烟味飘进五线谱。学生们突然安静了:“原来好音乐不是飘在天上的云,是踩在地上的泥。”
后来那场表演,没有炫目的灯光,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,唱到“山野的风”时,台下有学生跟着哼,最后一句落,半场教室都在抹眼泪。那之后,弯弯的月亮成了社团招新的“必考曲目”,甚至有理工科的学生,抱着吉他在图书馆楼下弹,说要“唱出衢州夜里的月亮”。
刘欢的歌里,藏着衢州人熟悉的“烟火气”
刘欢的音乐,和衢州有什么“化学反应”?
衢州人懂。这座城在浙西南,自古是“南孔圣地”,街巷里飘着孔庙的香火味,菜市场里能听见黄梅戏,就连喝茶都要配一碟“衢州烤饼”。刘欢的歌,从不是“高高在上的艺术品”——好汉歌里“大河向东流”的豪气,像衢江水的奔放;从头再来里“心若在梦就在”的倔强,像衢州人面对困境时,眉梢那股不服输的劲儿。
“我们学校有个‘非遗社团’,专门学衢州西安高腔,”小雨的指尖在琴键上跳,“指导老师说,刘欢的歌里有‘高腔的魂’——不是喊出来的,是从心里‘冒’出来的,像老茶农揉茶叶,得把劲儿揉进叶脉里。”
去年冬天,衢州下大雪,校园里的梅花开得正好。有学生在梅树下拍视频,背景音是教室里飘出的天地在我心,清亮的女声混着雪落的声音,发在网上后,有人评论:“这才是冬天该有的样子——有雪,有梅,还有刘欢歌里的‘天地’。”
当“刘欢的歌”成了衢州学院的“精神密码”
现在在衢州学院,“唱刘欢的歌”成了一种特殊“传统”。
新生军训的拉歌比赛,连理工科的方阵都会吼好汉歌;校庆晚会上,退休教师和00后学生合唱弯弯的月亮,白发和荧光棒在灯光下晃,有人偷偷抹了把脸;就连毕业典礼上,校长致辞前,全场都会起立唱从头再来,那句“心若在梦就在”,是学生们对这座城、这所学校最深的告别。
“刘欢的歌,不是‘流行符号’,是‘身份认同’。”教声乐的李老师说,“衢州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浙江周边,他们带着‘泥土气’来,在这里找到声音里的‘光’。刘欢的歌告诉他们:唱自己的故事,才是最动人的。”
前几天,小雨在朋友圈发了段视频:傍晚的操场,几个学生围坐在草坪上,弹着吉他唱千万次的问。镜头摇到远处,衢江闪着金光,像极了刘欢歌里那个“让我欢喜让我忧”的世界。
配文是:“我们唱的不是歌,是衢州的风,是衢州的月,是我们在这里长出来的根。”
写在最后:好音乐,从来都是“长”在土地里的
刘欢和衢州学院,看起来“风马牛不相及”。但你细听——那操场上飘来的歌声,那学生眼里闪着的光,那被音乐点亮的日常,不就是最好的答案?
好音乐从不是悬浮的。它像衢州的烂柯山,藏着千年故事;像衢江的水,滋养着岸边的生命。刘欢的歌之所以能一代代传下来,不是因为他有多“顶流”,而是因为他的歌里有“人”——有烟火,有泥土,有普通人想哭想笑的心。
而衢州学院的故事,也藏在这样的“烟火气”里。它不追求“网红式”的热闹,只是默默让每个学生明白:无论你来自哪里,唱出你心里的声音,就是最珍贵的“艺术”。
下次路过衢州,不妨去衢州学院转转。或许你就能听见,刘欢的歌,正在某个角落,和衢州的桂花香,一起飘进风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