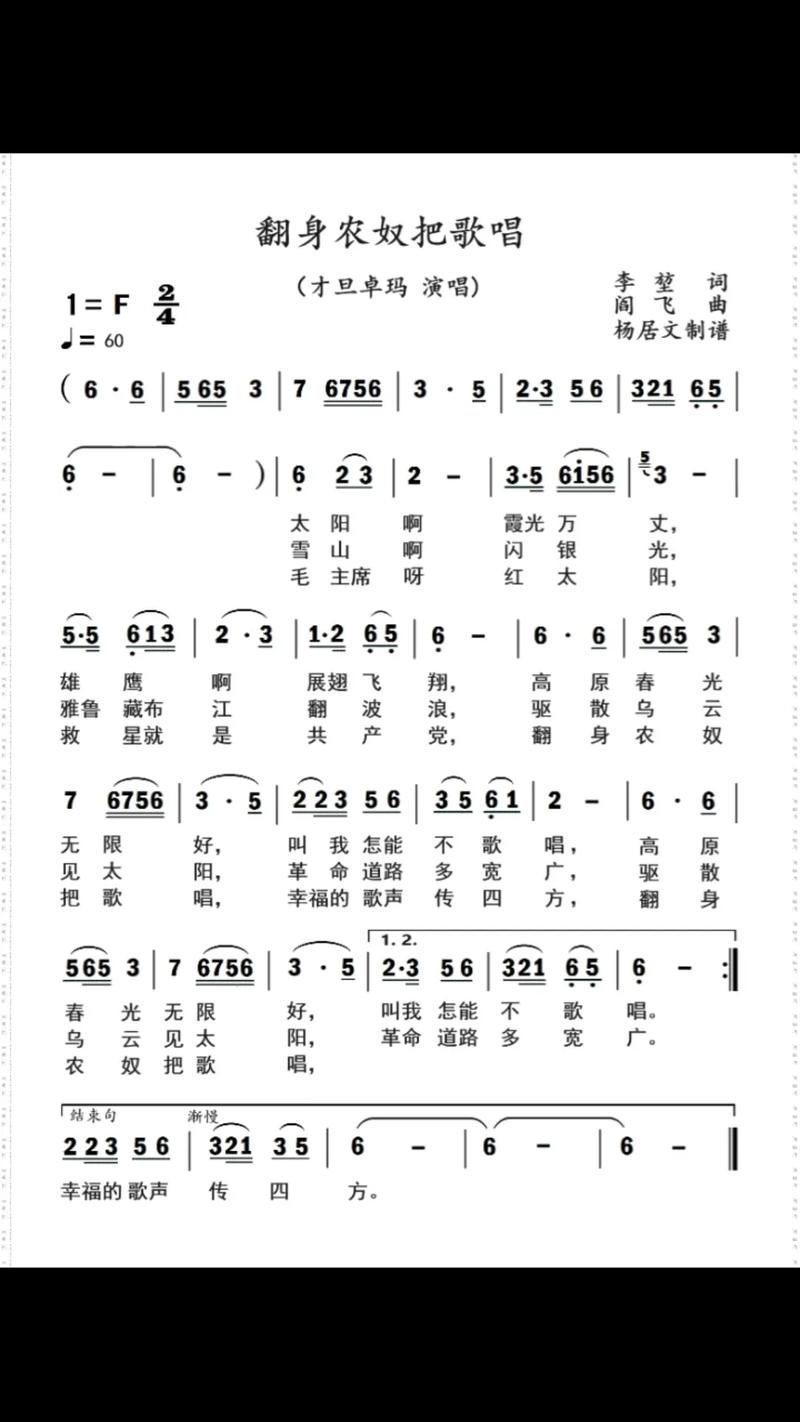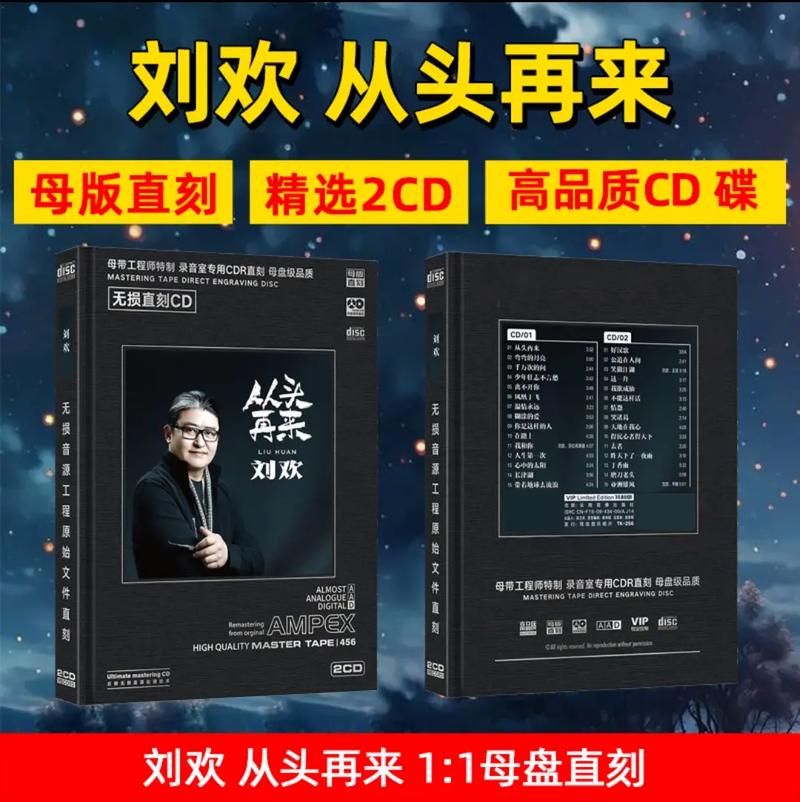说起来,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刷短视频,刷到周杰伦、林俊杰的老歌现场,评论区总飘着一句话:“那时候的歌手,是真的在唱歌。” 可要是仔细想想,比他们更“早”一辈的刘欢、羽泉、周华健、蔡健雅,好像连“怀旧”都显得多余——他们根本没“过气”,只是从流量舞台退回了音乐本身。

先说刘欢。这位在乐坛被称作“活化石”的男人,年轻时顶着“高音之王”的名号,一首弯弯的月亮能唱出江南水乡的温柔,好汉歌又是黄河水拍岸般的粗犷。可你搜搜他近年的采访,很少聊新歌,更多是在说“怎么教学生理解音乐”“怎么用科学方法保护嗓子”。去年声生不息里他重新唱千万次的问,没有炫技,就是微微低头,像讲故事一样把旋律铺开,台下连素来冷静的林子祥都跟着点头。有人说他“高冷”,可你看他在节目里听新人的作品,会拿着本子记和声走向,会蹲下来跟选手说“这个气口换在这里,情绪会更贴”。这样的“过气”,大概是乐坛最稀缺的“不合时宜”——他不是没热度,是宁愿把热度留给音乐本身。
再讲羽泉。当年最美一出来,“羽泉”两个字几乎成了“国民组合”的代名词,陈羽凡的中音温暖,胡海泉的高音清亮,两个大男生在舞台上绑着头巾唱“你知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”,愣是唱得全国中学生都在抄歌词。后来他们单飞了,闹过绯闻,走过低谷,可去年披荆斩棘的哥哥里,他们合唱世界由我造,陈羽凡的声音还是稳得像块磐石,胡海泉的和声还是像当年一样在主旋律上“贴”得恰到好处。后台采访陈羽凡说:“有人问我组合散了遗憾吗?我说不遗憾,因为我们写的歌还有人唱,还有人记得。” 羽泉的“过气”,大概是从“流量巅峰”退回了“创作初心”——他们不蹭综艺热点,不刻意卖情怀,只是隔两年就凑一张专辑,里面写的还是青春、梦想,普通人的生活。

周华健就更不用多说了。70后、80后的婚礼上,朋友是必放曲目;90后的KTV里,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永远在点歌单高位。去年他在北京开“少年侠客”演唱会,62岁的男人穿着长衫,抱着吉他唱孤泪英雄,唱到高音处还是能飙得让观众起鸡皮疙瘩。中场聊天,他说有次在商场听到小孩子唱朋友,跑过去一看,是四五岁的小孩,妈妈在旁边教他“朋友一生一起走”。周华健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:“原来有些歌,早就不属于我了,属于每一代人了。” 他的“过气”,大概是把“时代偶像”的位置,让了出来,自己却成了“时代的背景音”——就像空气,你平时感觉不到,可缺了,就会慌。
最后说蔡健雅。TANYA在华语乐坛,一直是“创作才女”的代名词,从陌生人到达尔文,她写的歌总能精准戳中心事。但和其他“前辈”不同,她的“过气”带着点“叛逆”——别人40岁唱苦情歌,她40岁玩电子乐;别人上综艺立“暖心姐姐”人设,她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直说“我写歌从不想讨好谁”。去年她发专辑DECADE,里面没有口水歌,全是实验性的编曲,采访里有人说“这样可能不火”,她挑挑眉:“火不火不重要,我想写十年后再听,还不觉得丢脸的歌。” 这样的“过气”,大概是在流量规则里“反其道而行之”——她不迎合市场,市场反而追着她跑,因为听众知道,蔡健雅的歌里,藏的是最真实的“她自己”。
说到底,刘欢、羽泉、周华健、蔡健雅的“过气”,不过是从“热搜常客”变成了“乐坛定海神针”。现在的娱乐圈,热搜每天都有新瓜,每天都有新人冒头,可歌单循环来循环去,真正能让人静下来听、听不腻的,还是他们写的旋律。不是因为“怀旧”,是因为他们的歌里有“真”——对音乐的真,对创作的真,对听众的真心。
下次再刷到他们的现场,不妨别划走。听听刘欢歌里的岁月沉淀,羽泉声里的兄弟情深,周华健调里的江湖侠气,蔡健雅词里的真实人生。或许你就会明白:有些歌手,从来不会“过气”,他们只是站在时间的另一头,让我们在喧嚣里,听见什么是“好歌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