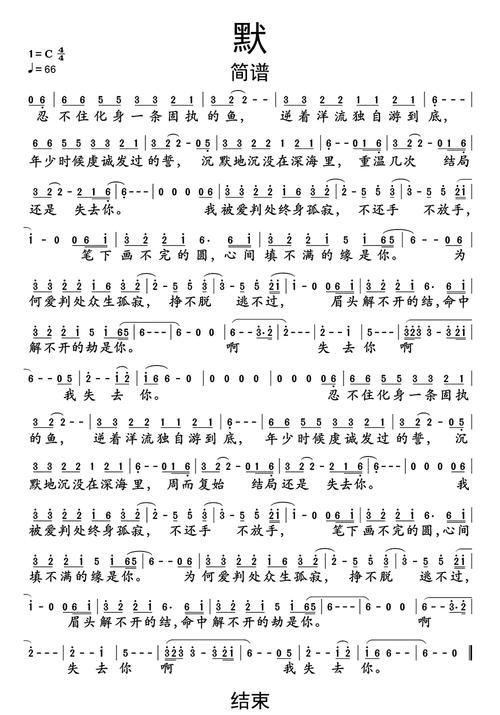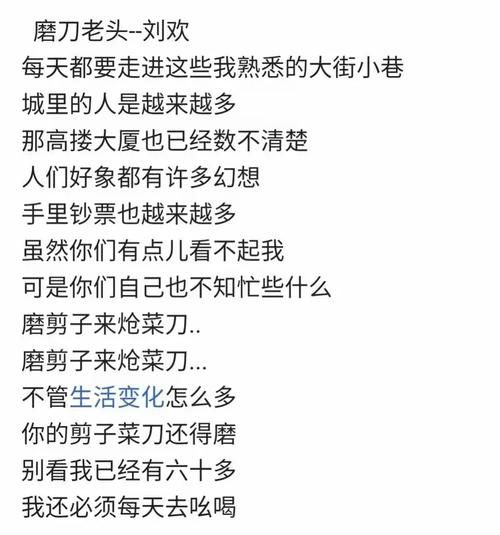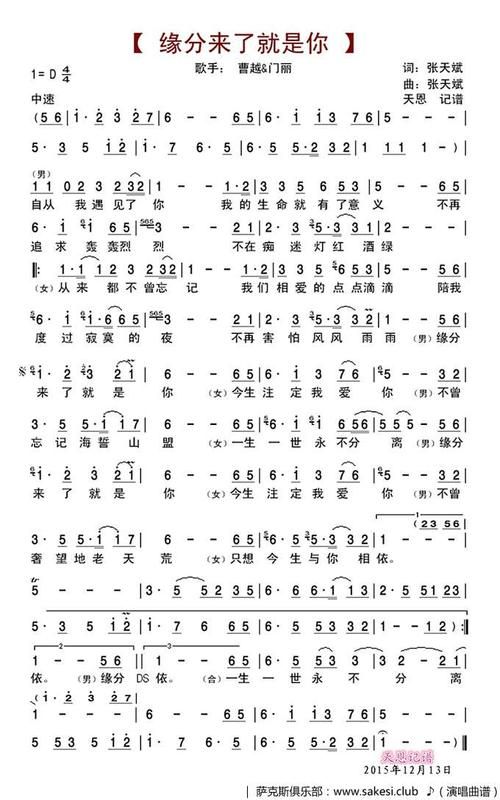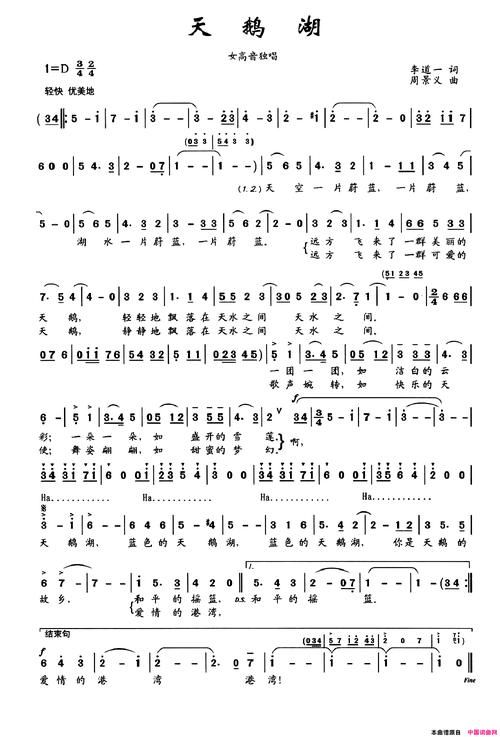要说信阳人骨子里刻着什么,大概是毛尖茶里的那份清冽,还有豫南山水赋予的韧劲。刘欢欢就是带着这股子劲儿从信阳茶山里走出来的——不是聚光灯下自带光环的“星二代”,也不是靠炒作博眼球的流量咖,硬是凭着一份近乎执拗的认真,在娱乐圈这个圈圈绕绕的地方,踩出了属于自己的脚印。
茶山里的童年:泥土里长出“戏痴”
信阳南湾湖的水,浉河港的风,养大了刘欢欢。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在茶山生活,春茶季凌晨四点就要跟着起床采茶,露水打湿裤脚,指尖被新芽扎出小口子,但她从不喊累。“那时候茶农们唱采茶歌,我就在旁边跟着哼,调子跑得十万八千里,他们也不恼,还笑说我‘嗓门大得能震飞麻雀’。”如今的刘欢欢聊起童年,眼里还闪着光,“可能那时候就开始‘偷学’了——学他们说话的尾音,学他们讲故事时眉飞色舞的样子,后来演农村戏,那些藏在大山里的记忆,突然就活了。”

真正让她迷上“演戏”的,是村里来了个拍纪录片的小剧组。她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,跟着摄像师傅跑遍了茶山的每个角落,看镜头怎么捕捉阳光,看演员怎么哭怎么笑。“有个阿姨演失去老伴的戏,就坐在茶垄里掉眼泪,我能闻到她身上泥土的味道,比任何台词都戳人。”那天回家,她对着镜子学人家哭,结果把自己哭笑了,却从此在心里种下了颗种子:“我也要当那样的演员,能让别人跟着我笑跟着我哭。”
北漂的“愣头青”:别人接偶像剧,她蹲剧组要馒头
18岁,刘欢欢揣着攒了好久的采茶工钱,背着半新不旧的帆布包去了北京。“当时啥也不懂,就想着得考个正经表演学校。”然而艺考之路并不顺利,身高不足、没系统学过表演,接连被几家院校拒绝。她没哭,在北漂出租屋里翻出信阳老家的信纸,给写了一封又一封信,终于在第三年,被一所民办艺术院校的表演系录取。
上学期间,她是出了名的“戏痴”。为了练台词,天不亮就去天坛公园读报纸,声音大到让晨练的大爷大妈都躲着走;为了观察生活,节假日蹲在胡同口看环卫工人扫地、听大爷下棋吵架,笔记本记了十几本;“别人周末约着去玩,我往各大剧组跑,从场务干起,搬道具、盯场记,就想看看真正的戏是怎么拍的。”有次跟组到横店,冬天拍夏戏,穿着短袖泡在冷水里,她冻得发抖却不肯喊“cut”,被导演夸“这娃有股憨劲儿”。
最惨的时候,她连续一个月没接到活儿,一天只吃两个馒头,但还是舍不得退掉北京的小出租屋——那里贴着她从茶山带出来的毛尖茶包装纸,写着“别丢了信阳人的韧劲儿”。转机出现在她大三,一个副导演看她蹲剧组啃干粮的样子,让她去试一个小配角,农村妇女,满嘴土话,还有哭戏。她没准备简历,就开口用信阳话唱了首采茶歌,又把自己采茶时被茶枝划破手臂的经历讲了一遍,最后哭着哭着,真的掉下了泪。“那个角色没台词,但导演说,‘你眼睛里有东西,是山里人的苦和倔’。”那是她第一次拿到片酬,没舍得花,寄给了茶山的奶奶,只留了10块钱,在路边小摊买了碗热汤面。
“实力派”不是标签,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
这几年,刘欢欢慢慢被观众认出来,不是因为上热搜,而是因为她演的角色——春风渡里被卖给地主的小媳妇阿莲,为了逃跑在雪地里爬了十几里路,指甲盖冻掉了也不吭声;山海情里援宁干部的老婆,抱着孩子在土窑洞里等丈夫回家,脸上的皱纹和方言都透着一股子“真”;岁岁年年里的乡村教师,三十年守在山区小学,眼神里的坚持让无数人落泪。
有回采访,记者问她“怎么看自己现在‘实力派’的标签”,她正蹲在片场帮道具师傅绑麦,笑着说:“啥实力派啊,我就是个‘戏痴’。小时候看茶农采茶,讲究‘一芽一叶’,得真真切切摸到那芽才行;演戏也一样,得真真切切当过那个人,说那句话,观众才能信。”她从不用替身,拍武戏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,拍文戏为了进入角色,真的去农村体验生活,“跟着大婶种地,挑扁担把肩膀都磨破了,但我知道阿莲是怎么挑起来的,这就值了。”
如今,她在北京买了小房子,屋里最显眼的还是信阳毛尖的茶罐,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,背景是连绵的茶山。“有人说我‘上升得太慢’,可我不急。茶还得慢慢炒呢,火大了就焦了,文火慢熬才有味儿。”最近,她刚接了个关于非遗传承的戏,讲的就是信阳毛尖的传统制作工艺,“能把家乡的故事演给全国看,比啥都强。”
从信阳茶山到聚光灯下,刘欢欢没经历过一夜爆红的奇迹,却用茶农炒茶的耐心,一步一个脚印,把角色“熬”成了自己的样子。或许在流量横行的时代,这种“慢”本身就是一种实力——不投机,不取巧,只带着信阳人的韧劲儿和泥土里的真诚,演好每一个“小人物”。毕竟,真正能让人记住的,从来不是刻意打造的标签,而是刻在骨子里的“真”与“韧”,就像她最爱的信阳毛尖,初尝清淡,回味里,全是岁月的回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