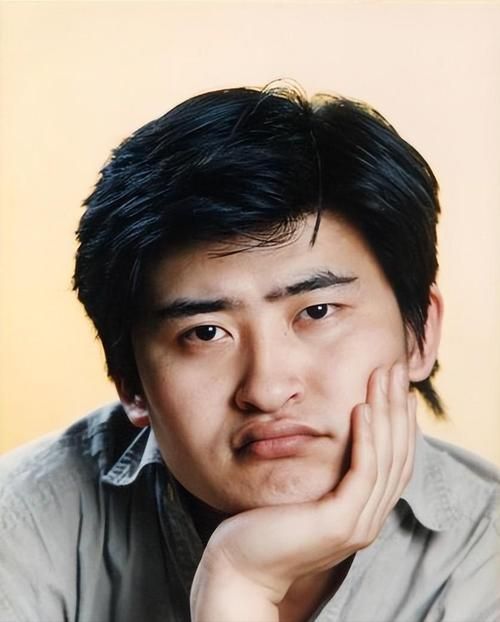前几天刷后台,有粉丝私聊问:“为什么有些歌词一听就上头,回头细看却平平无奇?反而有些歌词乍看挺直白,越品越有味?”
我突然想起三年前刘欢在歌手后台,点评某首竞演歌曲时说的话的一段旧采访。当时有记者问他“现在的歌词是不是越来越追求‘金句’了”,他放下手谱,指着歌词本里的某一句说:“好歌词不是‘炸’在一两句,是把人心里的褶皱熨平了——你听着觉得‘啊,原来是这样’,不是因为词多聪明,是它替你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,变成了可以摸着的东西。”
先说说“王炸歌词”的迷思: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上头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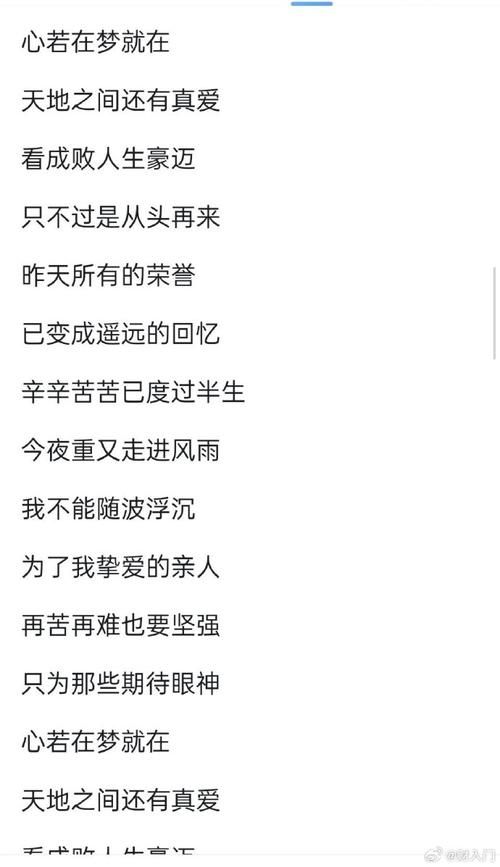
这几年乐坛挺有意思的,好像不整几句“金句”都不好意思叫“神作”。有的是主打画面感的“晚风踩着云朵赴约”,有的是带点哲理的“我们都在阴沟里,但仍有人仰望星空”,还有的是用大白话扎心的“不是所有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”。
这些歌词确实能第一时间抓住耳朵,但问题来了:为什么有的“金句”听三遍就腻,有的却能让人单曲循环时,总忍不住回头看词?
刘欢在节目里说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:“歌词像泡茶,有的茶一冲就出味儿,浓得呛嗓子;有的茶得慢慢泡,第一口平淡,第二口回甘,第三口才能品出山头和季茬。”现在很多歌词,就是“冲太急”的茶——为了“炸”,硬凑意象、强押韵,结果看着热闹,咽下去寡淡。
刘欢眼里“真正会炸”的歌词,从来不止“写得好”
作为音乐圈公认的“活字典”,刘欢参与制作的音乐从弯弯的月亮到甄嬛传主题曲,几乎每个时代的爆款都有他的影子。他对歌词的挑剔,圈内人众所周知——曾有个当红歌手拿着写好的歌词找他改,结果他一句话把对方问懵了:“你写这句的时候,自己心里动了一下吗?”
他点出的“王炸歌词”的共性,从来不是华丽辞藻,而是三个“藏得住”的功夫:
第一,藏得住“人”的温度——不是作者在说话,是听者在照镜子
刘欢总说“歌词是骨肉相连的旋律”,但他更强调“骨肉”得有“人的体温”。举个很老的例子,罗大佑光阴的故事里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我们”,你要是只看字面,会觉得“太直白了”。但为什么能火几十年?
因为不是罗大佑在回忆青春,是每个听的人都能在这句词里,塞进自己的青春——可能是小学操场的夕阳,可能是毕业照上的傻笑,可能是某个没说再见的夏天。刘欢在采访里提过:“当年录这首歌,我特意让编曲放轻,就是怕太复杂的旋律抢了词里的‘留白’——留白不是空,是给听者填自己故事的地方。”
反观现在有些歌词,满眼“我踏碎山河”“我笑饮千愁”,听着很燃,但关掉音视频,你能记住哪个画面吗?没有具体的人、事、情绪,再华丽的词都是“纸老虎”。
第二,藏得住“俗”的智慧——把大白话熬成老火汤
很多人觉得“有深度的歌词就得文绉绉”,刘欢直接泼冷水:“能把‘俗话’说到人心窝里,才是真本事。”
他举过毛不易消愁的例子:“一杯敬朝阳,一杯敬月光”,这两句词要换成“玉盘”“朱曦”,可能显得“有文采”,但毛易-bu用了最家常的“朝阳”“月光”,反而让整首歌的愁绪有了烟火气——不是那种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愁,是一个普通人在小酒馆里,对着日常的日出日落,跟自己和解的愁。
刘欢当时说:“现在很多年轻人写词,怕‘俗’,拼命往里塞生僻字、典故,结果词和听众之间隔了层纱。真正的好歌词,得像街坊聊天——你听着觉得‘这不就在说我嘛’,才叫到位。”
第三,藏得住“韵”的呼吸——别为了押韵,让词在“喘不上气”
韵脚是歌词的“骨架”,但骨架太硬,肉就撑不起来了。刘欢在经典咏流传制作苔时,就特意跟作曲家说:“原词‘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’,韵是‘ai’,但如果每句都死磕‘ai’,听久了会累。咱们可以在第二句‘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’这里,稍微‘松’一点,像人说话换口气似的。”
结果呢?这两句词传得最广,就是因为韵脚自然得就像苔花自己在说话——不是词作者写的,是苔花“长”出来的韵。
反观现在某些歌词,为了“押上韵”,硬凑“月亮”“翅膀”“远方”,明明前后逻辑不通,却因为“押韵”就硬塞进去。刘欢对此直接评价:“押韵是给歌词添彩的,不是给歌词定框架的。为了韵牺牲意思,就像给鞋子镶钻,结果把鞋底硌穿了,还穿啥鞋?”
说到底,“王炸歌词”的“王炸”,从来不是“炸”给耳朵的,是“炸”给心的
写到这里,突然理解为什么刘欢的话能戳中这么多人——他不教人怎么写“爆款词”,只提醒我们“别丢了词的本心”。
歌词这东西,本质上和说话一样。那些让人一听就记住的词,不是因为它多惊艳,而是它在你心里“挠了一下”:可能是你反复想说的那句话,你憋了半天的情绪,你差点就忘了的某个瞬间。
就像刘欢最后在采访里说的:“音乐人别总想着‘造金句’,想想你写这首歌时,是为了给谁唱。你唱的是自己,听的人就会代入;你唱的是故事,听的人就会共鸣;你唱的是真心,听的人就捂不住心窝子。”
所以下次再听到“王炸歌词”,不妨多听两遍:它炸的,是那一瞬间的“懂”;而这份“懂”的背后,藏着一个词人,把普通人日子里的光,熬成了糖。